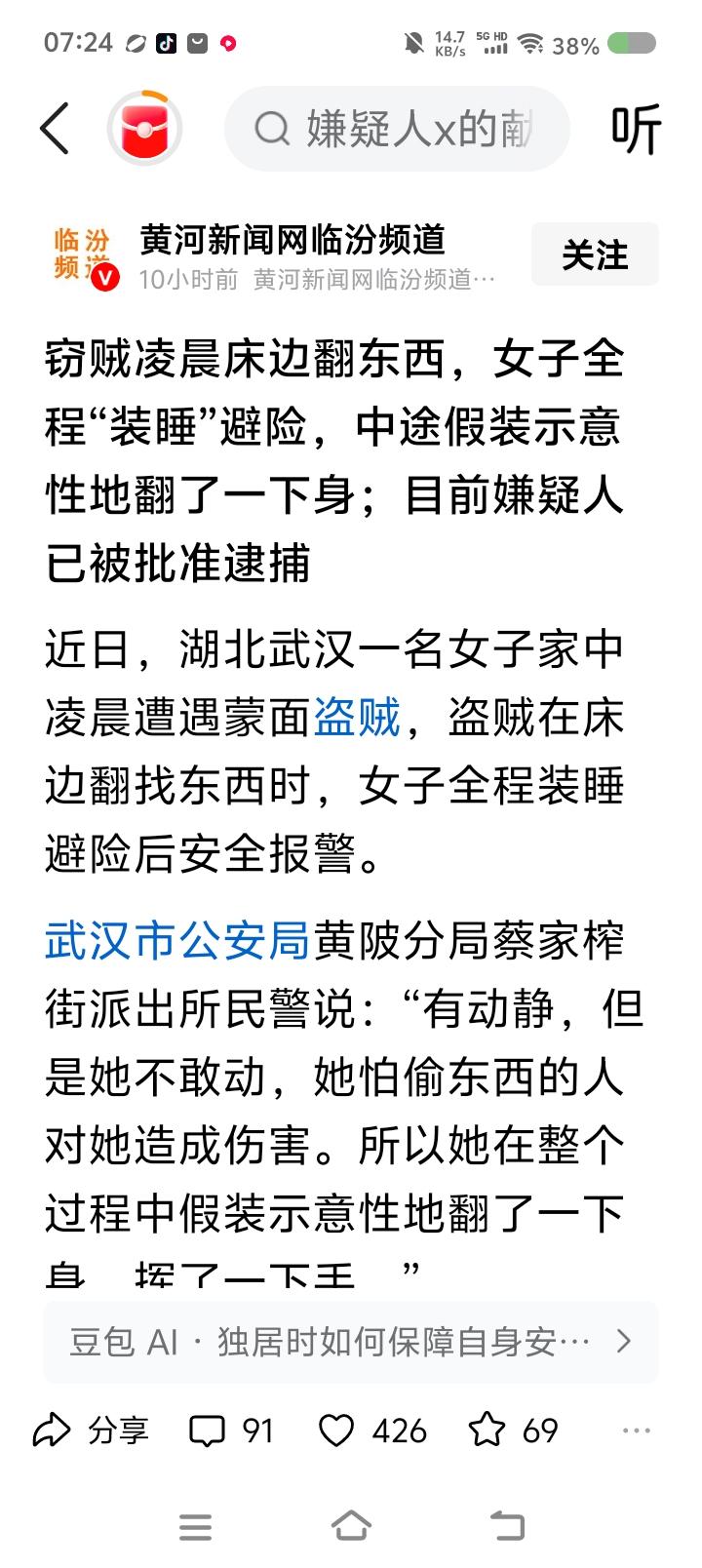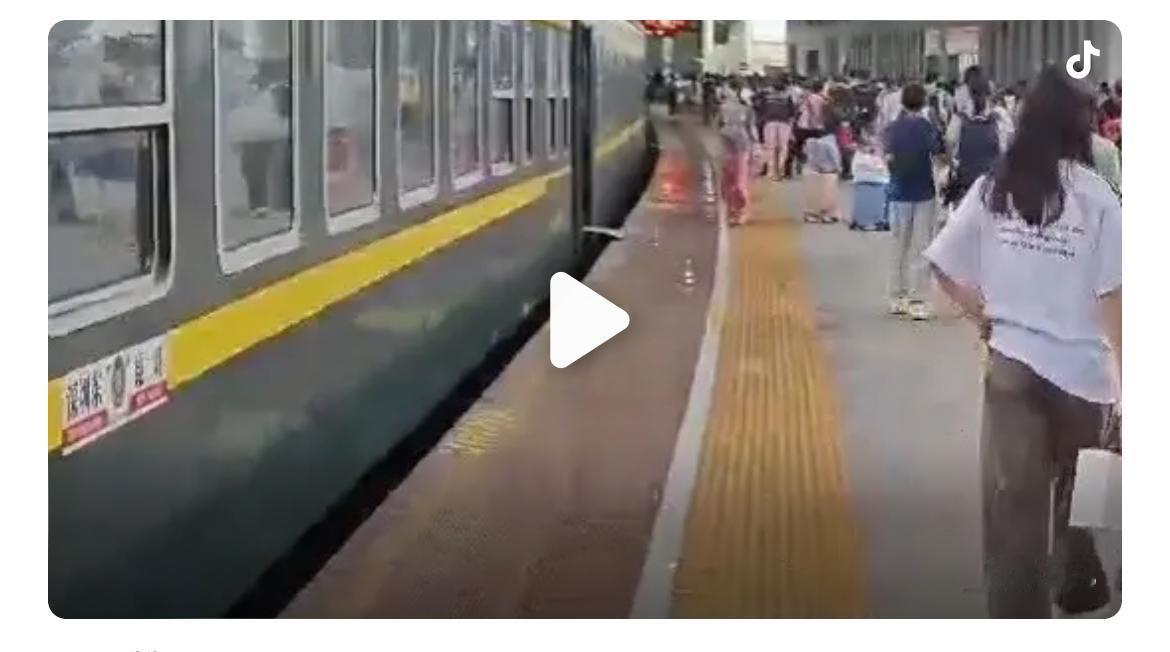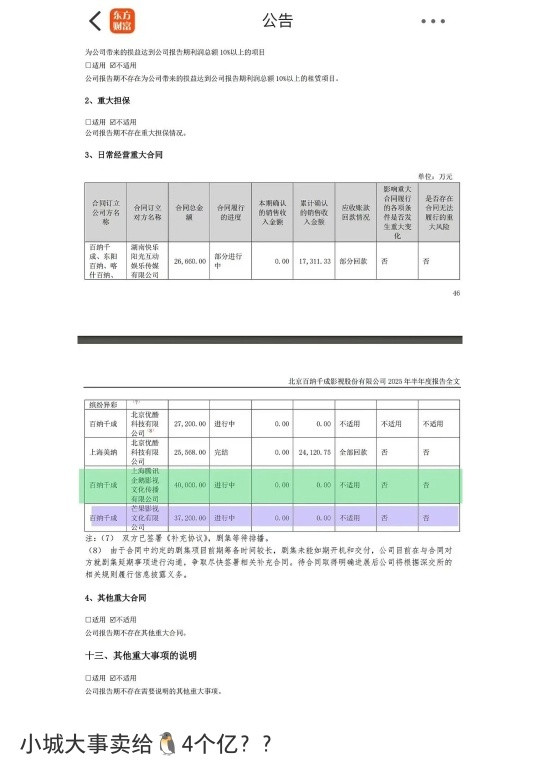姑姑今年七十八,头发白了大半,可腰板挺得笔直。 没退休金,姑父前年走的时候,就留下老城根那栋带院儿的平房。大伙儿都劝她去儿女那住,她总笑着摆手,说自个儿的窝住着踏实,不给孩子们添乱。儿子在深圳敲代码,电话里永远伴着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女儿嫁城西,女婿跑运输常不在家,还得接送上小学的外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开春的时候,姑姑把院子里枯了的老枣树砍了,腾出地方摆了俩旧藤椅,又从废品站淘了张掉漆的方桌。每天早饭后,她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守着巷口卖自家腌的糖蒜。一罐五块钱,玻璃罐是攒的酱菜瓶,洗得透亮,标签都擦干净了。 起初巷里人好奇买回去尝,都说这糖蒜甜辣适口,比菜市场卖的还对味,没多久就传开了。邻街的张阿姨每天都来买一罐,说配白粥绝了;放学的小屁孩路过,也会拽着大人的衣角要“奶奶的甜蒜”。姑姑收钱时总眯着眼笑,把零钱叠得整整齐齐塞进布兜里——那布兜是姑父生前给她缝的,针脚有点歪,却结实得很,用了快二十年。 有回儿子放假回来,看见她蹲在院门口剥蒜,指甲缝里全是蒜汁,鼻子一酸就要接过来帮忙。姑姑把他的手推开:“别碰,蒜辣手,你那敲代码的金贵手可不能沾。”晚上吃饭时,儿子说要给她请个保姆,姑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我手脚麻利着呢,雇人得花多少钱,你留着给你媳妇买奶粉,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女儿上个月提了箱牛奶来,看见院子里堆着半袋大蒜,又念叨着要接她去城西住。姑姑拉着她的手往屋里走,掀开炕头的布帘,露出一坛封好的糖蒜:“这是给你腌的,知道你爱吃。你家那小阳台,连个腌蒜的地方都没有,我在这住着,还能给你们腌点零嘴,哪天想吃了就来拿。” 前几天我去看她,正赶上她给糖蒜封口。阳光透过院墙上爬的喇叭花架,落在她的白头发上,闪着细碎的光。她抬头看见我,赶紧塞给我一罐刚封好的:“回去配面条吃,香着呢。”我接过罐子,冰凉的玻璃上还沾着她的体温。 巷口的风慢悠悠吹过,带着糖蒜的甜香,姑姑又坐在藤椅上,低头剥起了蒜,腰板依旧挺得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