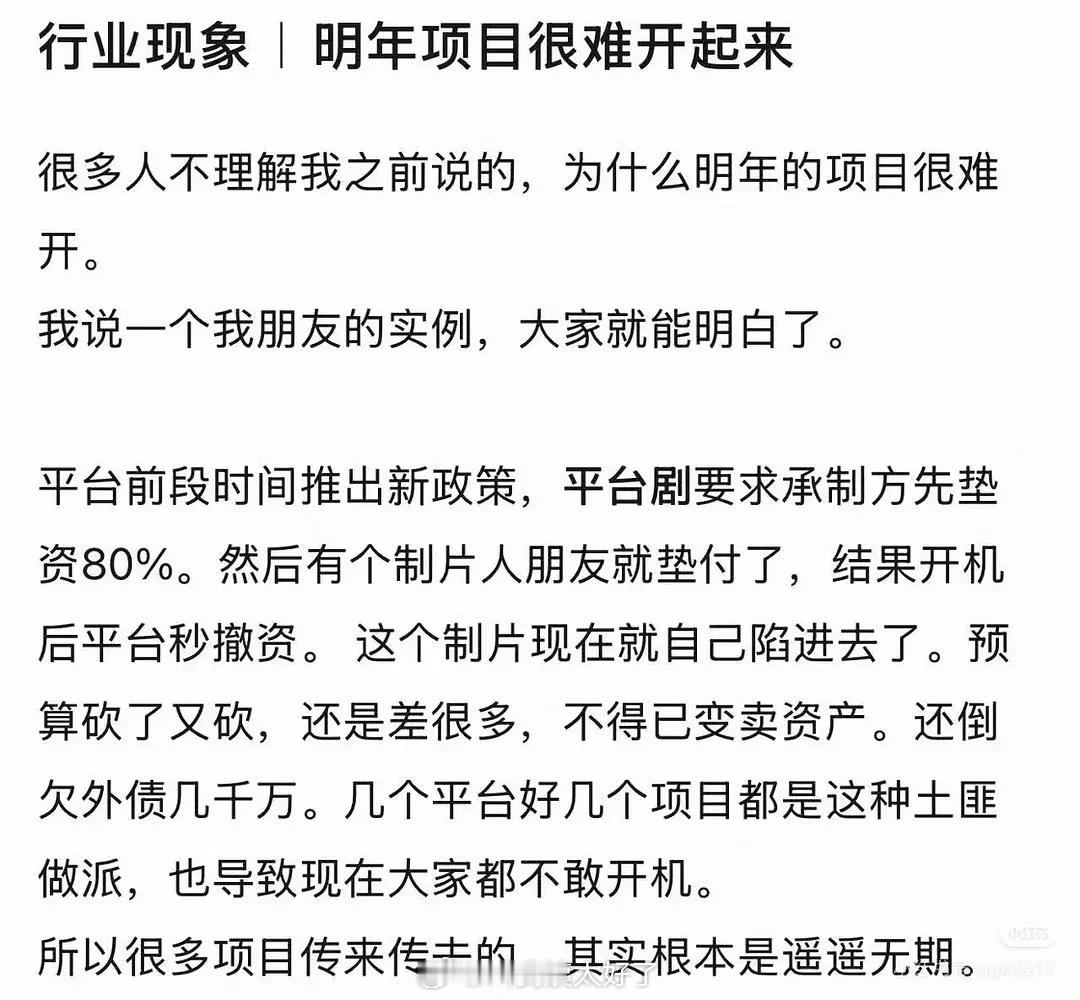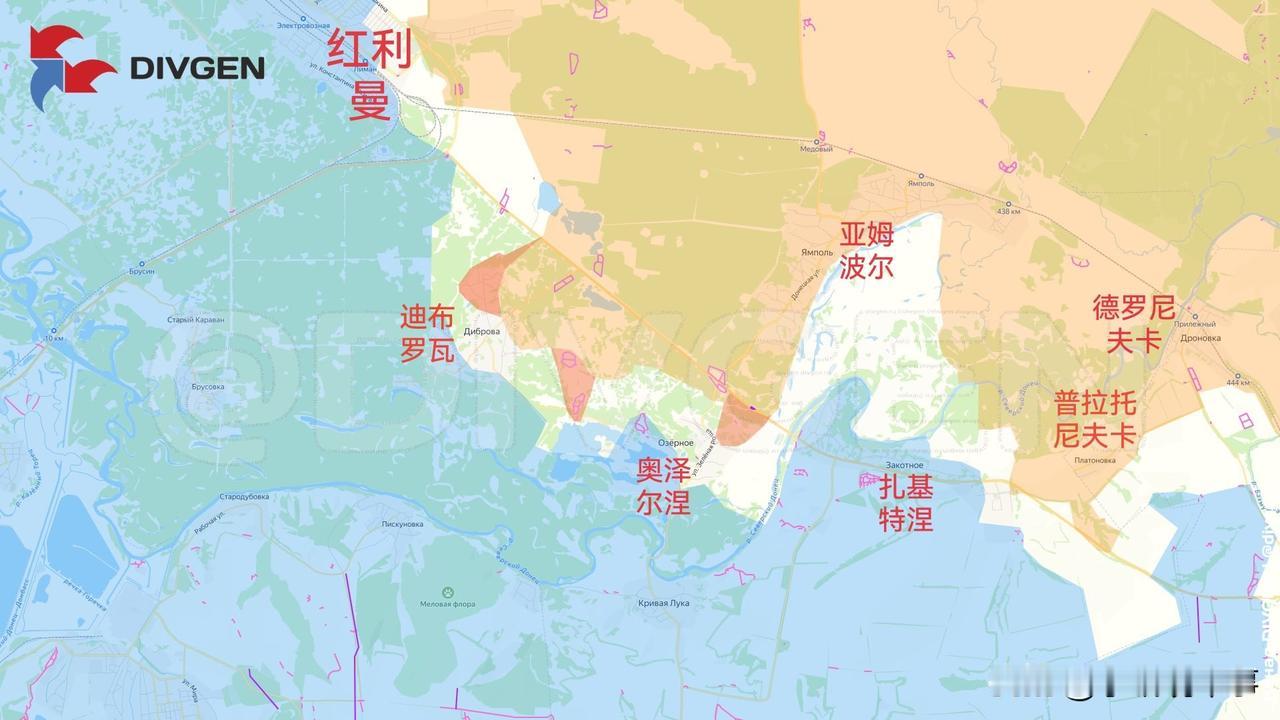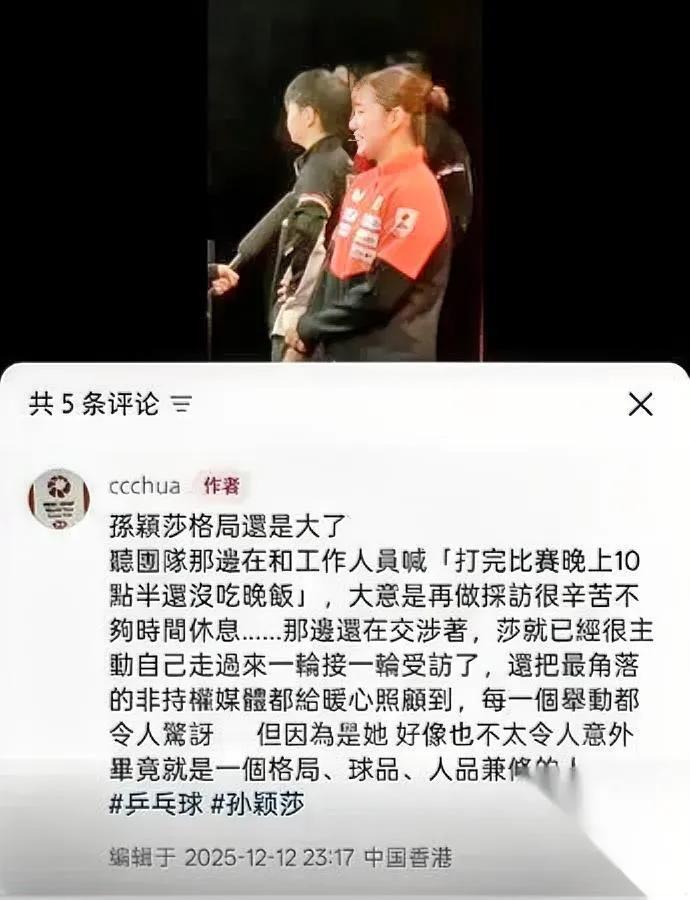我的亲叔叔,这次中风了,我装不知道。这话要是让我妈知道,非得拿鸡毛掸子抽我不可。可我攥着手机,看着堂哥发来的“爸突发中风,在市一院抢救”的消息,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半天,终究还是没回,甚至把聊天记录往上一划,假装没看见。我和叔叔的疙瘩,结了快十年了。 手机在掌心发烫,堂哥的消息像根刺,扎得我眼睛生疼。“爸突发中风,在市一院抢救”——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像道解不开的数学题。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指甲盖都泛白了,最终还是划走了对话框。我妈要是知道这事,准得提着鸡毛掸子从老家杀过来,可我现在只想当只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 十年前那个夏天的味道突然涌了上来。也是这样闷的天,我蹲在叔叔家楼下的台阶上,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蝉鸣吵得人心烦,我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他摇摇晃晃地从麻将馆出来,衬衫领口沾着油渍。 “叔,我考上大学了,差五千块学费。”我声音发颤,像蚊子哼哼。他斜睨了我一眼,从裤兜里摸出个瘪钱包,数了三张十块的扔给我:“自己想办法,我家也不宽裕。”硬币滚到我脚边,阳光反射的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后来才知道,那天他刚输了八百块,却给堂哥买了最新款的游戏机。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堂姐发来的:“医生说情况不太好,你有空来一趟吗?”我把手机倒扣在桌上,玻璃屏映出我模糊的脸。桌上的仙人球刺扎手,就像叔叔当年那句“你爸走得早,我当叔的也不容易”。是啊,他不容易,我爸走那年我才八岁,他把我家的老房子占了,说给我存着娶媳妇,转头就改成了他儿子的婚房。 厨房传来我妈切菜的声音,咚咚咚,像是在敲我的心。她总说:“那是你亲叔,血浓于水。”可水也分冷的热的吧?那年我发高烧,给他打电话想让他送我去医院,他说在忙,结果我在急诊室看见他陪着堂哥买球鞋。护士扎针的时候我没哭,看见他拎着球鞋盒子从门口经过,眼泪倒掉了下来。 “小宇,发什么呆呢?”我妈端着菜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我赶紧把手机塞进口袋,含糊地说没事。她突然叹了口气:“你叔那人,就是嘴硬心软。当年你爸治病,他偷偷塞给我的钱,我到现在都没还。” 我愣住了,筷子差点掉地上。怎么从没听她说过? “他不让说,怕你婶知道了闹。”我妈坐下,眼神飘向窗外,“你叔年轻时候也苦,十五岁就出来打工,供你爸读书。后来你婶身体不好,家里开销大,他也是没办法。”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医院的照片。叔叔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头发白了一大半,看着像个陌生人。记忆里那个总是挺直腰杆的男人,怎么突然就老了? 我想起小时候,他总把我架在脖子上,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糖。阳光穿过树叶,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他说:“小宇要好好学习,以后带叔去大城市看看。”那时候他的笑声,比蝉鸣还响亮。 手指终于动了,点开对话框,输入又删除。最后只回了两个字:“地址。”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眼泪突然掉了下来,砸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一片模糊的光。原来有些疙瘩,不是解不开,只是我们都忘了,当初为什么系上它。 去医院的路上,阳光很好。我买了束康乃馨,护士说病人需要安静。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叔叔正好醒着,看见我,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嗬嗬的声音。我把花放在床头柜上,握住他枯瘦的手,像小时候他牵着我那样。 “叔,我来了。” 他的手指动了动,好像想回握我。窗外的风进来,带着夏天的味道,这次不闷了,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