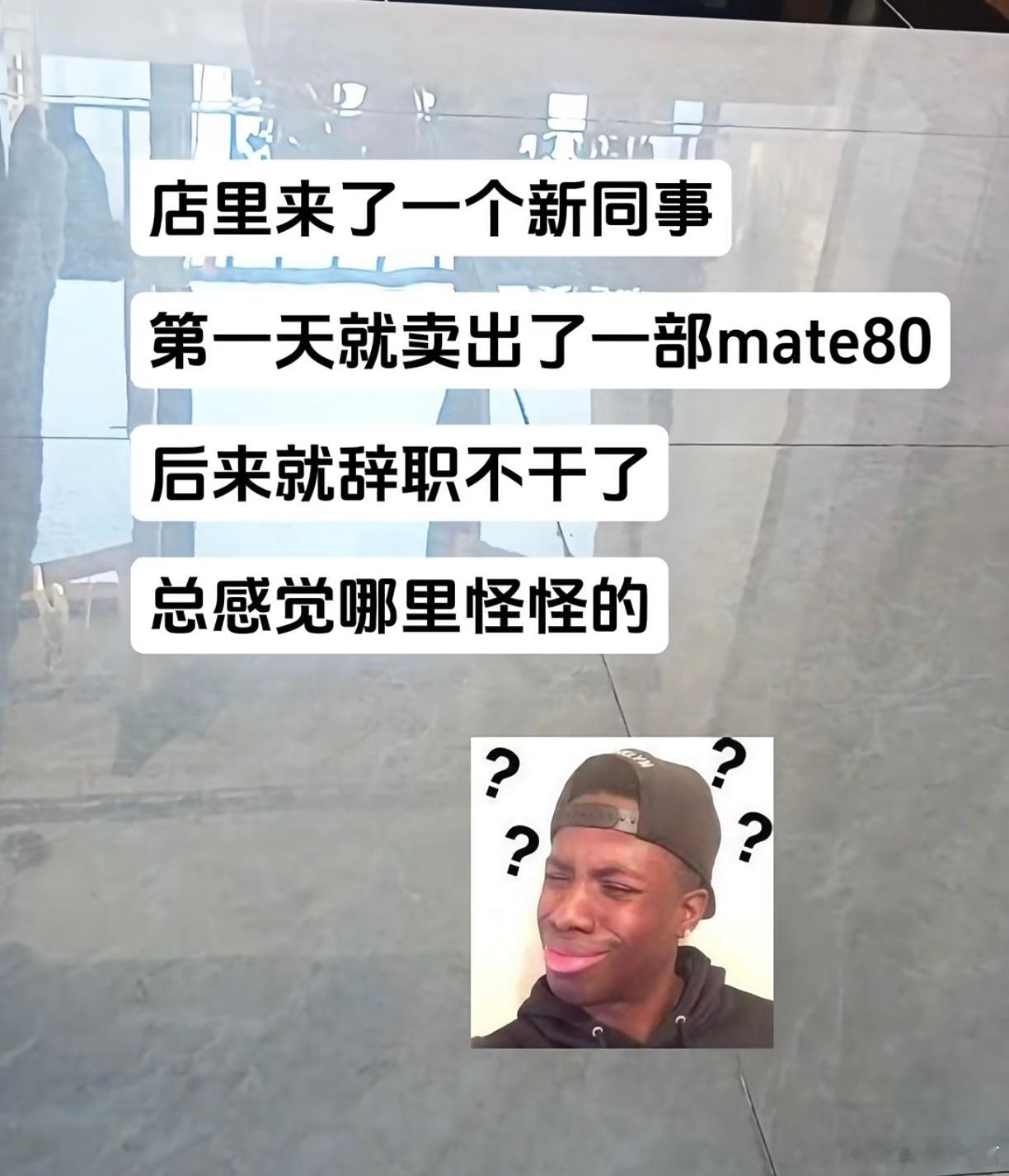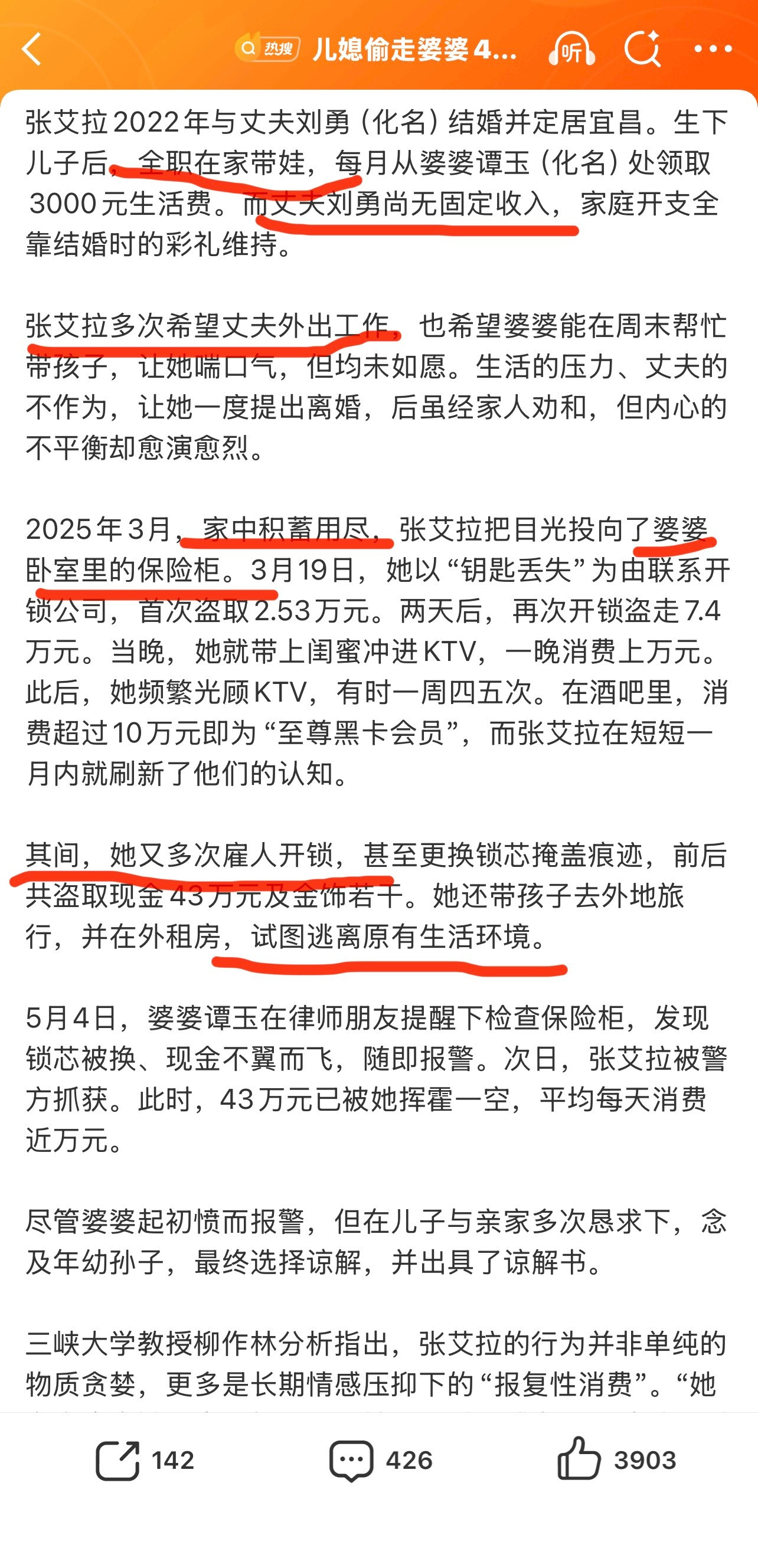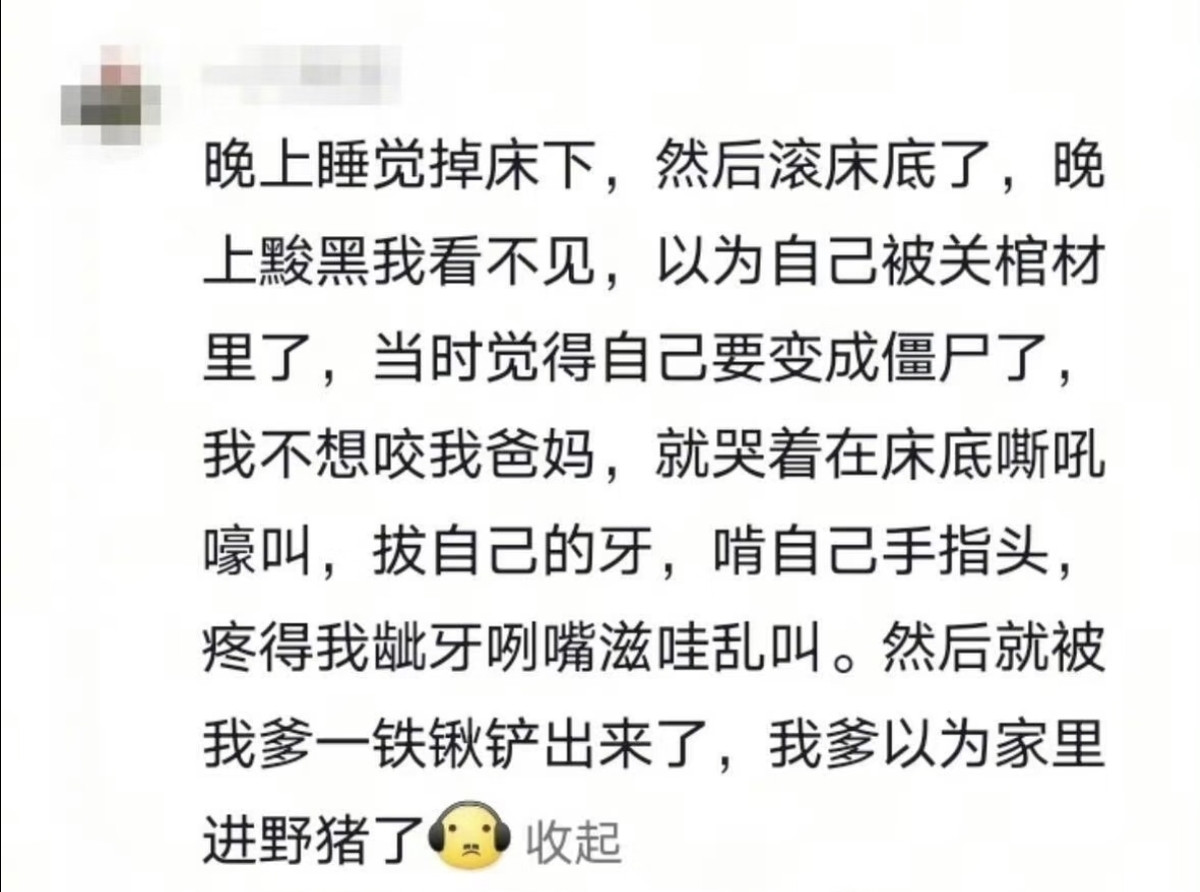我和老公吵架,老公让我滚,我拿起身份证,立马找了个民宿打工,管吃管住。连续一个月给我发消息,我一条都没回。让他一个人过快乐生活。民宿在山脚的老院里,老板陈姨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见我拎着个布袋子站在门口,直拍我手背:“先住下,活儿不急着干。” 吵架那天的声音还在耳朵里打旋,他说“滚”的时候,唾沫星子溅在我脸上,带着刚喝完的啤酒味。 我没哭,转身去卧室翻抽屉,身份证边角被磨得发毛——那是结婚时一起去办的,照片上两个人笑得像傻子。 布袋子里只装了这张身份证和一件换洗衣物,走到楼下才发现,连手机充电器都忘了拿。 山脚的老院藏在竹林后面,木门虚掩着,飘出柴火和晒干的艾草味。 我站在门口攥着布袋子,指节发白,陈姨从院里出来,头发花白绾成髻,见我这样,直拍我手背:“先住下,活儿不急着干。” 她手心糙,带着老茧,拍得我手背上一阵暖,像小时候奶奶给我搓冻疮。 陈姨没问我从哪来,为什么只拎个布袋子。 每天早上她都端来一碗热粥,粥面上浮着层米油,中间卧着个溏心蛋——是她自己养的鸡下的,蛋白嫩得轻轻一戳就破,蛋黄流出来,金灿灿的,像撒了把碎阳光。 我负责打扫客房,床单要晒在院里的绳子上,老梨树枝桠横在绳子上方,风一吹,床单鼓起来,蹭着梨树叶沙沙响。 手机在布袋子底层震动了一个月。 从第一天的“你在哪”到第十天的“我错了”,再到第三十天的“妈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屏幕亮了又暗,我一次都没点开。 直到那天整理最里间客房,枕头下掉出本旧相册,翻开第一页,是陈姨和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站在这老院门口,老头搂着她肩膀,两人笑得眼睛都眯了,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1985年冬,她赌气回娘家,我揣着俩热馒头去接,在村口站到脚冻僵,她才从门后探出头,说‘馒头凉了’。” 原来所有的决绝,都藏着等一个台阶的柔软? 我蹲在地上翻相册,手指划过老头的脸——和陈姨现在的样子很像,都是眼角堆着笑纹。 陈姨走进来,递过一杯热水:“那是老王,走了五年了。”她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晒着的床单,“年轻时总吵架,他嘴笨,吵急了就说‘你走’,我偏走,走到村口又怕他真不找我,就蹲在老槐树下等,一等就是半宿。” 我突然想起那天他让我滚,我摔门走时,好像听见他喉咙里有个破音,当时只当是气急败坏,现在想来,会不会也是怕? 布袋子挂在梨树上,风吹得它晃悠,里面的身份证边角还在磨,可现在多了串钥匙——陈姨给的,铜的,串着个红绳结,是她自己编的,说“住下了,就得有个开门的东西”。 手机又震了,这次我没忍,掏出来看,屏幕上是他发来的照片:床头柜第一个抽屉拉开着,里面有个丝绒盒子,我的戒指躺在里面,旁边压着张纸条,字歪歪扭扭的:“我把灰擦了。” 那戒指,是结婚一周年他送的,我摘下来半年了,总说“戴着干活碍事”。 手上的薄茧是劈柴磨的,陈姨说“劈柴能解气”,我信,现在劈得比谁都快。 只是今晚晒的被子没收,躺在上面能闻到阳光和艾草的味,还有点梨花香——老梨树要开花了。 手机屏幕还亮着,他刚又发了条:“我买了新的床单,你喜欢的那种蓝格子,就是不知道尺寸对不对,要不……你回来量量?” 手指悬在“回复”上,窗外的月光落在手背上,像他以前给我暖手时的温度。 布袋子里的红绳结钥匙硌着腿,我想,明天早上得跟陈姨学学编红绳,编两个,一个挂钥匙,一个……或许能寄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