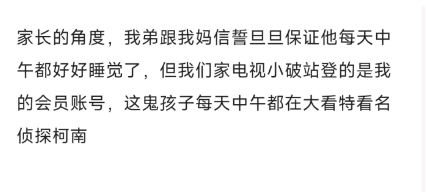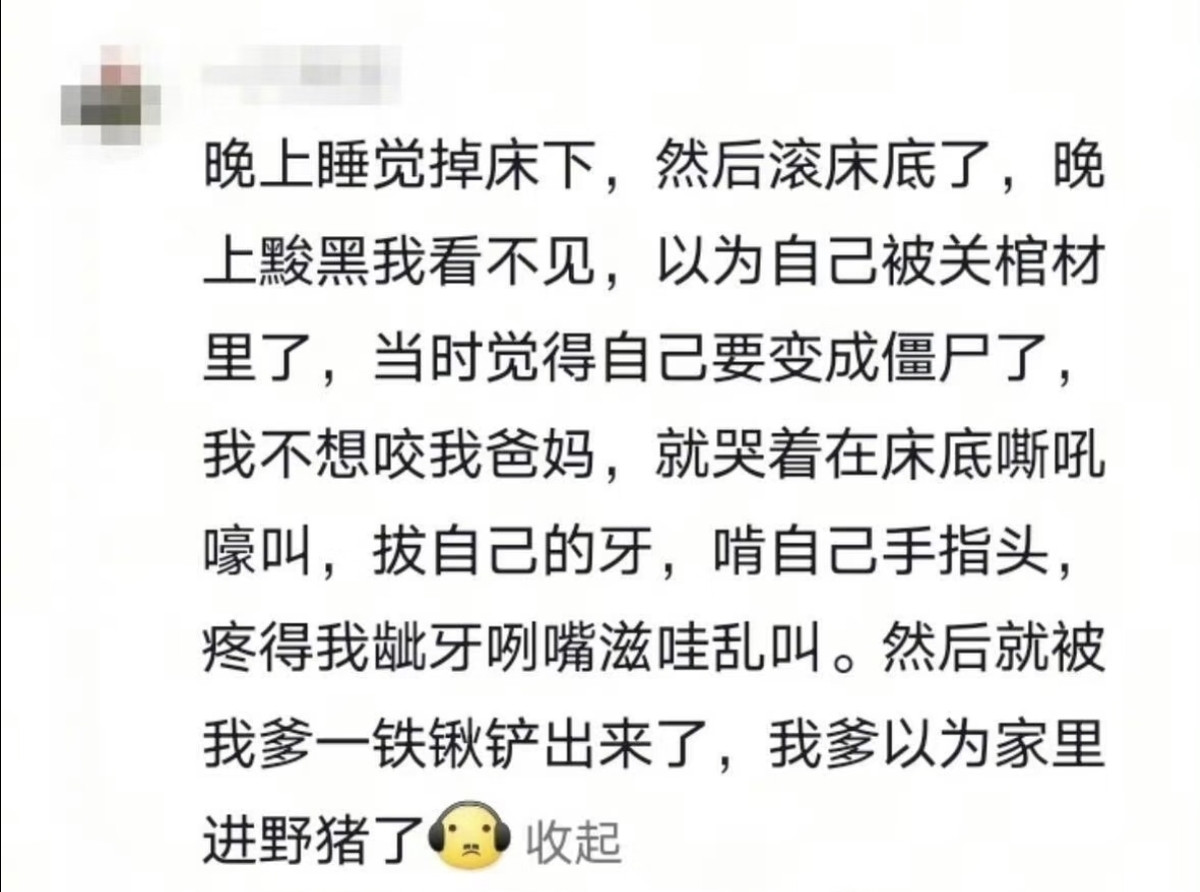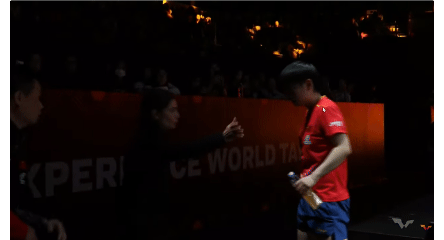村里有位中年妇女,下地打药的时候,天气酷热难耐,她就在一个沟里洗了澡。这妇女叫秀莲,四十出头的年纪,皮肤是常年跟土地打交道晒出的深褐色,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田埂上蔓延的裂纹。这天日头毒得邪乎,玉米叶子卷着边儿,打药桶压在肩上像块烙铁。她瞅着沟里刚下过雨积的水,绿幽幽的漂着几片柳叶,咬咬牙脱了外衣就跳了进去。 秀莲在四十出头的年纪,皮肤早被日头和汗水腌成了深褐色,像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红薯,带着土腥味的暖。 这天日头毒得邪乎,玉米叶子卷着边,绿得发黑,打药桶压在肩上,铁皮贴着肉,烫得人直抽气。 她从早上五点下地,到日头爬到头顶时,嗓子眼早干得像塞了团干草,每走一步,药桶晃一下,药水顺着桶壁流到背上,又辣又烫。 走到玉米地尽头那条沟时,她看见积水了——前两天下过雨,水绿幽幽的,漂着几片柳叶,像谁撒了把碎翡翠。 她停下脚,瞅着那水。村里老人常说“沟里的水脏,有蛇”,可此刻背上的汗黏得像胶水,药桶的铁箍快嵌进肉里了。 她往四周望了望,玉米秆高得能藏住人,东边的坡上没人,西边的路上也没人。 咬咬牙,她把药桶往地上一墩,“咚”的一声惊飞了沟边的蚂蚱。 脱外衣时手都在抖,不是怕,是急——急着把这身汗臭和疲惫,都泡进那点清凉里去。 后来她跟人说这事,总有人笑她“不讲究”,一个女人家在野地里洗澡。 她只是嘿嘿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像被水泡过的纸——谁没在日头底下渴过?谁没在累得直不起腰时,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喘口气? 那桶药水有三十斤重,她从村东头背到村西头,玉米叶子划得胳膊生疼,药水熏得头疼,可比起这些,日头晒在脊梁上的疼更难熬,像有无数根细针在扎,扎得她只想把自己浸进凉水里,哪怕只有一分钟。 你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在土里刨食,在汗里打滚吗?可谁规定,刨食的人就不能偷片刻清凉? 那天她在沟里泡了不到十分钟,水凉得激骨头,可爬上来穿衣服时,浑身的骨头缝都松快了。 从那以后,她再遇到毒日头,就会想起沟里的水——不是逃避,是知道再硬的身子,也得有处软乎地儿歇脚。 她重新背起药桶时,桶好像轻了点,日头还是毒,可她觉得,深褐色的皮肤上,好像有了层水的凉,正一点点往肉里渗,跟土地的暖,慢慢融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