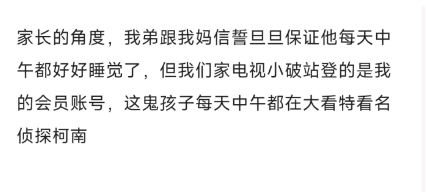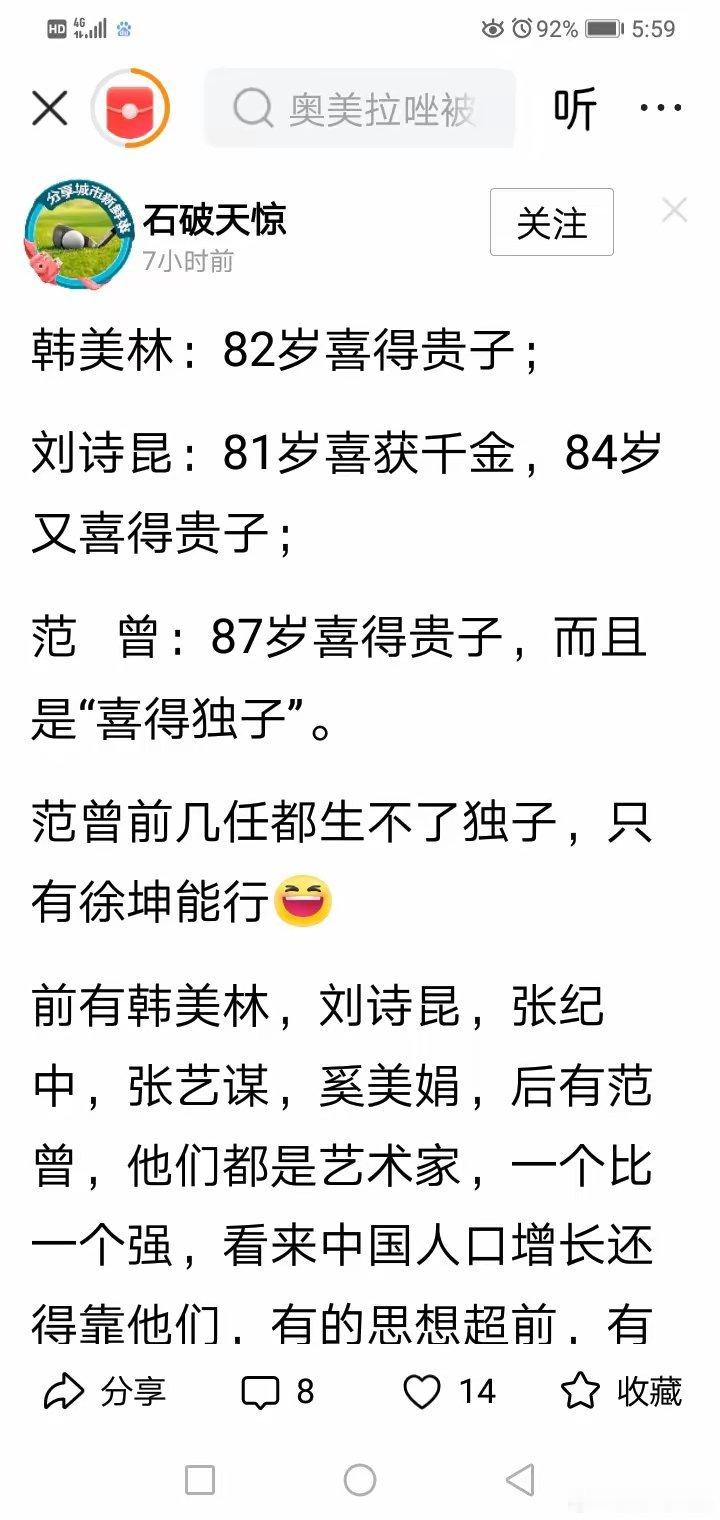我女儿在家洗碗一次要五块钱,已经洗了半年了。儿子今天说他也想洗,而且只要三块钱。让我把姐姐辞退。我告诉姐姐:你升职了,当监工。正在写作业的女儿猛地抬起头,铅笔尖在练习册上戳出个小黑点。她把马尾辫甩到身后,眼珠子转得飞快:“监工是干啥的?比洗碗挣得多不?” 晚饭的碗还在水槽里泡着,泡沫堆得老高,像朵懒洋洋的云。女儿系着卡通围裙,正踮脚够吊柜里的洗洁精——这是她的“工位”,半年了,每个碗碟从她手里过一趟,我微信里就多一笔五块的转账。 儿子突然从客厅跑过来,小皮鞋在瓷砖上打滑,一把抓住我的裤腿:“妈妈,我也想洗碗!”他仰着脖子,鼻尖上沾着点饼干渣,“我只要三块!比姐姐便宜!” 我正擦着灶台的手顿了顿。水槽里的泡沫“啵”地破了个小泡,女儿的背影僵了一下,手里的洗洁精瓶子没拿稳,“哐当”磕在台面上。 “那姐姐呢?”我故意问。 儿子眼睛一亮,像发现新大陆:“把姐姐辞退!我比她便宜!” 客厅里,女儿的铅笔尖在练习册上猛地一戳,纸面立刻洇开个小黑点。她猛地抬起头,马尾辫甩到身后,橡皮屑簌簌落在桌沿:“妈!他说啥?” 我走过去,把她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姐姐升职了,当监工。” “监工?”她手里的铅笔“啪嗒”掉在桌上,眼珠子转得飞快,像揣了只小兔子,“监工是干啥的?站着看吗?比洗碗挣得多不?” “当然。”我憋着笑,指了指水槽边跃跃欲试的儿子,“监工要检查弟弟洗的碗干不干净——碗沿有没有油星子,盘子底有没有饭粒,洗完的碗碟要码整齐,要是不合格,就得让他重洗,还能扣他工钱呢。” 女儿“唰”地站起来,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几步冲到厨房门口,叉着腰瞪儿子:“听见没?我是监工!你要是敢偷懒,我就扣你钱!” 儿子正往水槽里挤洗洁精,闻言手一抖,半瓶洗洁精“咕嘟”全进去了,泡沫瞬间漫过水槽,像要溢出来的棉花糖。他慌了神,转头冲我喊:“妈!她欺负人!” “谁欺负你了?”女儿立刻弯腰,用手指戳了戳一个刚洗完的碗,“你看!这里还有油!重洗!”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泡沫里姐弟俩的小影子。女儿的马尾辫一晃一晃,认真得像个小老师;儿子噘着嘴,却还是乖乖拿起抹布,对着碗沿使劲擦。 其实我知道,女儿这半年洗碗越来越用心,上次我感冒,她还偷偷把我的保温杯也洗了,杯底的茶渍擦得锃亮;儿子呢,上周在超市盯着奥特曼卡片看了半天,回来就问我“怎么才能挣钱”,大概是把洗碗当成了“兼职”。 那天晚上,儿子洗完最后一个碗时,胳膊都酸了,女儿却拿着我的手机,一笔一划记“监工日志”:“3月12日,弟弟洗碗:碗沿有油×2,扣5毛;水槽没擦干净,扣5毛;共计2元。” 儿子凑过来看,急得跳脚:“凭啥扣这么多!我洗了八个碗!” “八个碗有五个不合格!”女儿把手机举高,“监工说扣就扣!” 后来的日子,厨房成了姐弟俩的“小战场”。女儿每天写完作业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她的“监工日志”本——就是那本戳了小黑点的练习册,后面几页全画着歪歪扭扭的碗和对勾;儿子洗碗时总偷偷往泡沫里藏玩具车,想让姐姐找不到,结果每次都被女儿从泡沫堆里扒出来,然后名正言顺地“扣钱”。 有天我听见女儿在房间里算“工资”:“这周弟弟表现不错,只扣了一块五,我挣了五块监工费,比洗碗多两块呢!”儿子在旁边哼哼:“等我学会洗快点,我就不当洗碗工了,我要当总监工!” 我笑着把刚切好的苹果放在他们桌上,练习册上的小黑点旁边,女儿后来画了个咧嘴笑的小人,旁边写着:“监工也不容易呀。” 原来孩子的世界里,“辞退”和“升职”不过是场带着泡沫的游戏,而藏在游戏里的,是他们偷偷学着长大的样子——女儿开始懂得“责任”不是随便站着看,儿子明白了“便宜”换不来偷懒的权利,而我,不过是在泡沫漫出来时,轻轻递了个装着阳光的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