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一个医生,为什么要主动毁掉自己的身体?手术室的灯照着她苍白的脸,护士握着止血钳的手都在抖。 刚切除扁桃体那几天,她连喝水都疼得掉泪,现在又要拔掉满口好牙,同事劝她“留几颗吃饭吧”,她只摇头:“发炎一次就要耽误半个月研究,我等不起。” 拔掉牙齿后,陈菊梅戴上假牙就回到了实验室。 那时肝炎是医学界的硬骨头,慢性重型肝炎病死率超过八成,患者家属送来的感谢信常常还带着泪痕。 她带着团队在中药库里一筛就是八年,五味子的藤蔓爬满窗台时,终于发现提取物能降转氨酶。 有患者昏迷半个月,用上她研发的制剂后突然睁开眼,拉着她的手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她背过身擦了擦眼镜,镜片上的雾气半天没散。 2003年春天,SARS病毒像一阵黑风刮过京城。 70岁的陈菊梅收拾行李住进隔离病房,防护服密不透风,她低血糖犯了就啃块巧克力,护士要替她查房,她摆手:“我看过的病人,我心里有数。” 有次给重症患者插管,飞沫溅到护目镜上,她事后用酒精棉片擦了擦,继续记录病程。 后来学生问她怕不怕,她翻出泛黄的工作笔记,指着1972年那页说:“从拔牙那天起,我就没怕过什么。” 汶川地震那年,80岁的她踩着胶鞋在灾区走了二十多天。 北川的雨下个不停,她带着人在安置点挖排水沟,泥浆灌进鞋里,她说“脚泡肿了没关系,疫情控制住才行”。 有个孕妇发烧,她撑着伞走两公里去看,确认不是传染病后,从包里摸出颗糖塞给对方:“安心养着,孩子出生了告诉我。” 后来那家人寄来孩子的照片,背面写着“陈奶奶,您的糖真甜”。 她的白大褂袖口磨出了毛边,工资卡上的钱总在月初就少一大笔,多半是给了贫困患者。 女儿说她“对自己抠门到家”,她却把实验室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全是给加班同事准备的牛奶面包。 96岁临终前,她躺在病床上签遗体捐赠书,手抖得握不住笔,护士要帮忙,她摇头自己写:“这点力气,还是有的。” 晚年整理她的遗物时,同事发现一个旧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为了病人,本钱可以‘透支’”。 这句写于1972年拔牙后的话,和她96岁签下的遗体捐赠书,连在一起就是一位医者最完整的答卷,把每一寸生命,都用在了需要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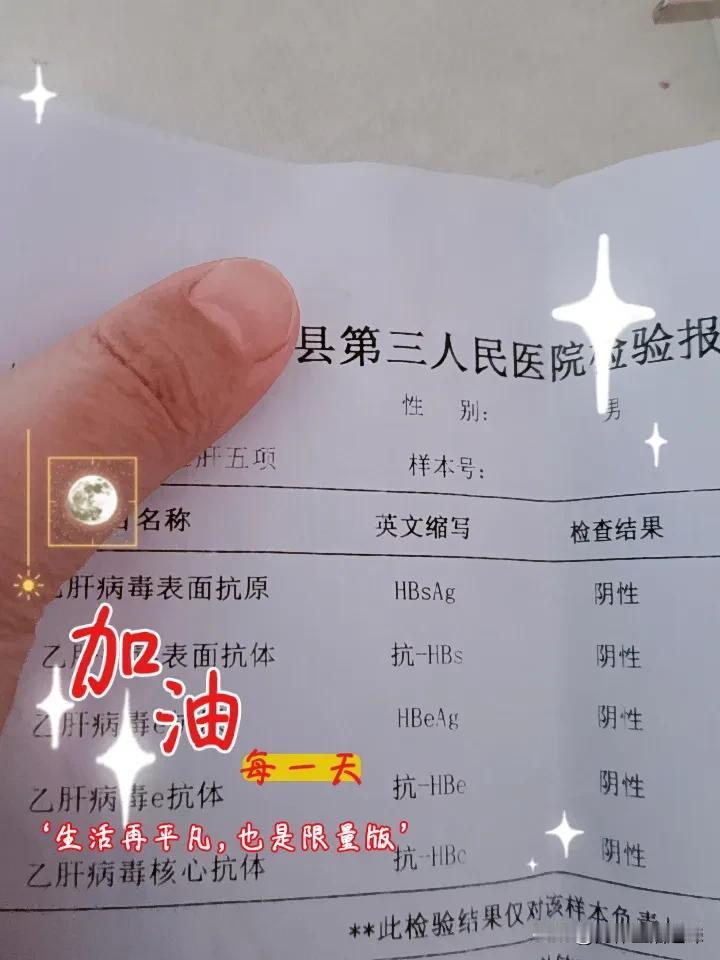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