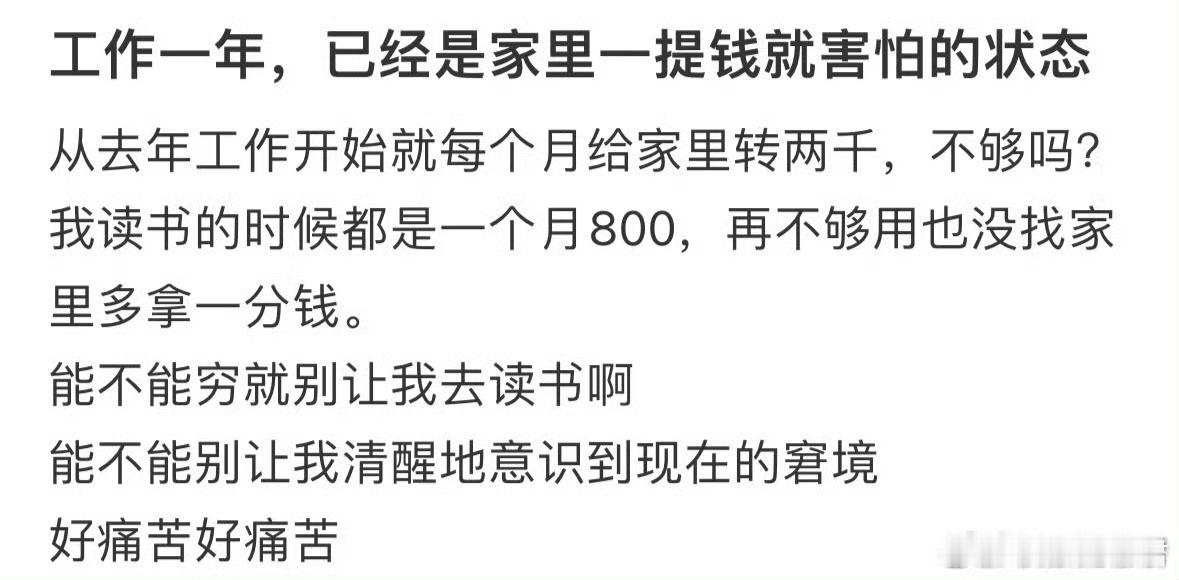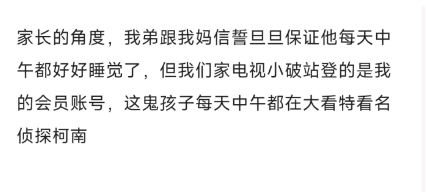因为我家井水旺,邻居们浇地都争先恐后的用,谁先浇谁后浇,用着用着水泵坏了。那天下午我正在院里晒玉米,就听见东头的李婶在井台边喊:“咋没水了?”跑到井边一看,水泵的电源线还插在插座上,电机却连点动静都没有。 院角的老井打我记事起就没干过,入夏后井台边更没断过人——东家李婶的豆角该搭架了,西头王伯的玉米该灌浆了,连村尾的小辉都扛着水管来浇他那半分菜畦。 井绳磨出的毛边总沾着各家的泥点,有时是李婶家黄瓜架的青灰,有时是王伯鞋上带的麦糠,偶尔还缠着小辉菜畦里的狗尾草。 那天我正把玉米摊在院里晒,金黄的颗粒滚得满院都是,阳光晒得它们发烫,抓一把能闻见生熟之间的焦香。 东头突然传来李婶的大嗓门:“咋没水了?” 我扔了木锨往井台跑,远远看见她正踮着脚够水泵开关,蓝布衫后襟沾着片草叶——那是今早去摘豆角时蹭的。 水泵的电源线还插在插座上,塑料壳被晒得烫手,我按了按开关,电机闷着一声都不吭,像头累瘫的老牛。 谁弄坏的?这话在喉咙里滚了滚没敢说,毕竟这泵开春时就有点杂音,只是大家急着用水,谁也没在意。 李婶蹲下来摸了摸电机,“怕是烧了”,声音软了半截,“这阵子天旱,我今早五点就来抽,估摸着是我用太久了。” 我蹲下去看插座,线脚处有圈黑痕,心里突然一软——她去年秋收时还帮我家抢收玉米,露水打湿了裤脚都没歇着。 其实前晚我起夜,看见王伯打着手电在井台边捣鼓,当时以为他在接水管,现在想来,怕是早发现泵不对劲,只是没好意思说。 共用一口井的日子久了,谁都觉得“先用先用”是本分,却忘了铁打的泵也经不住连轴转;就像李婶总说“你家井旺,该多帮衬大家”,却没算过她自己偷偷换过三次井绳。 那天下午没修成泵,李婶回家翻出她男人生前的工具箱,王伯扛来他儿子寄的新电线,小辉抱来半箱冰镇汽水——井台边突然比有水时还热闹。 后来泵修好了,井绳换成了新的尼龙绳,李婶在绳头系了个小铃铛,谁家用水,铃铛一响,井台边就有人探出头问“够不够?” 原来共用的不是井水,是日子——你帮我扶一把泵,我替你看一眼绳,水就一直旺着。 傍晚收玉米时,我抓了把晒得焦香的颗粒撒进井里,听见井底传来“咚”的一声轻响,像极了那年李婶帮我收玉米时,玉米掉进竹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