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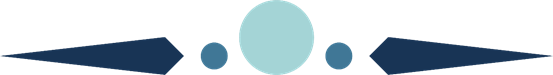
Hi~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宫读书会,上期我们看完了上篇的资本市场开场,这期我们就来看看中篇的内容,资本是如何让市场变得更加壮大和复杂。
对欧洲的资本持有者而言,革命与战争从来不是灾难,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饕餮盛宴。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像一道裂缝,让金融家们钻了进去——瑞士银行家族在幕后推动高息放贷合法化,押注拿破仑上台,换得丰厚回报;英国巴林家族斡旋法国战后赔款,靠承销公债赚得72万英镑,稳稳坐上欧洲“第六强权”的位置;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凭着密网般的信息渠道,提前接住滑铁卢的战报,不动声色地囤积英国国债,这笔投机的价值,放到今天大概超过6亿英镑。
这些沉淀下来的利润,后来都变成了铁路的枕木、工厂的烟囱和轮船的螺旋桨。成千上万的工人走进厂房,机器的轰鸣里,一个以财富为标识的新精英阶层慢慢站了起来——银行家、商人、实业家,他们取代了旧贵族的位置。曾经不可一世的土地贵族发现,庄园的边界在慢慢缩小,为了保住体面,只好放下身段与新富阶层通婚。英国通过1832、1867、1884年三次选举改革,一点点削弱贵族的政治权力,议会里的话语权,渐渐落到了资本家手里。
与光鲜的新精英形成对照的,是窝在阴暗潮湿工棚里的工人和童工。传染病在拥挤的住处蔓延,他们把痛苦都算在机器头上,阿克赖特的工厂遭到袭击。工会的领导者们慢慢明白,没有政治力量撑腰,工联主义不过是风中的口号。直到1924年,工党组成英国首届政府,这种失衡才稍稍有了转机。
18世纪晚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到英国,很快捕捉到工业生产里的金融痛点:货物运出去,要等两个月才能拿到一张三个月后才能兑换的票据。他们一家家银行地跑,筛选更划算的贷款和贴现率。1815年英法战争后,这个家族开始涉足各类工厂,起初对铁路持怀疑态度,错失英国市场后,便迅速转向欧洲大陆,同时把手伸进采矿、黄金、铜、钻石和石油领域。这种规模的扩张,需要更灵活的资本组织方式,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形,就在这样的需求里慢慢浮现。
现代股份公司的成长,像一场漫长的解冻。从中世纪到阿克赖特的工厂,合伙制一直是主流融资方式,无限责任被视作一种信用保证——可这种保证也成了枷锁,限制了企业的筹资能力,一旦有合伙人去世,整个企业可能就跟着垮掉。16、17世纪的“特许公司”比如东印度公司,靠着皇家授权的垄断权,成了权贵掠夺海外财富的工具,它们有复杂的组织架构,部分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股票能转让,寿命长得惊人。直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独占权被取消,1856年,英国正式确立有限责任制度,创办公司不必再求国家特许,股东只需以股份为限承担责任,这道枷锁才算彻底解开。
资本市场的工具,总是先从稳妥的开始。债券比普通股票更早被大众接受,毕竟有固定回报、有担保,能让人睡得安稳。19世纪20年代,可转换债券出现,铁路公司几乎全靠发债募资,股票更像一种未来的期许。高杠杆终究藏着风险,大量铁路公司破产,破产重整的过程里,收入债券、浮动利率债券等新品种接连冒了出来。
优先股是种奇怪的混合体,兼有债券和股票的特质,能拿固定股息,也能分红利,代价通常是放弃投票权。在英国,推行优先股是为了限制铁路公司债务规模,避免控制权被稀释;在美国,它成了原有股东保住话语权的工具。20世纪初,并购浪潮催生了巨型工业公司,普通股才慢慢流行起来,第一批公众投资者也随之出现。股东不再是企业的主人,更像一个旁观者,A类股、B类股、管理股这些设计,都是为了适配这种转变。美国曾在20年代禁止无投票权普通股上市,直到1985年,纽交所才放宽“一股一票”的要求,给了新型科技公司上市的空间。

资本的狂欢里,总有危机在暗处等着。1844年的英国铁路热,更像一场集体投机游戏:几个人组成委员会,发认股广告,雇工程师勘测路线,向议会申请许可,然后发行股票认购凭证——认购者只需付10%的钱,余款等修建时再缴。很多人根本没打算缴余款,只想高价转卖凭证。等到催缴通知下来,认购证的溢价瞬间蒸发,股市从狂热跌入萧条。资金从正常商业渠道流失,银行破产,危机蔓延到法国,那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50%。英国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也埋下了周期性危机的种子。
18世纪末,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英国的工业资本家从底层崛起。国内市场很快饱和,他们急需打开海外大门,传统的帝国思维,慢慢被以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帝国思维取代。资本主义站稳脚跟后,不仅控制人的劳动,还开始渗透思想——一套以利润为核心的伦理体系,规定了政治运行、法律边界,甚至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当利润成了唯一的目标,就再没有伦理能制衡它,资本权力,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
即便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英国还是迎来了空前的发展。1851年,伦敦水晶宫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一半展品都来自英国,那是它工业霸权的顶峰。但模仿者很快跟上,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相继走上工业化道路,美国和德国后来居上,英国的独霸地位慢慢丧失,工业资本的收益越来越薄,资本开始撤离工业领域。工业发展像一条单行道,一旦被技术、产业路径锁死,企业会被淘汰,国家也会走向衰落。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19世纪的中国,资本的脚步走得磕磕绊绊。1823年,英国商人来到广州,首要拜访的就是怡和行掌门人伍秉鉴——当时清廷实行“一口通商”,只有广州能做外贸,十三行制度“以商代官”,行商既是商人,又是准官员,形成了垄断格局。到1834年,伍秉鉴的财产达2600万银元,比当时的美国首富还要富有。
当中英关系紧张时,伍秉鉴想给自己买两份“保险”:花巨资捐了三品顶戴,又成立“于仁洋面保安行”,允许华商附股——华商们愿意附股,不过是想找个法律更健全的靠山,躲避朝廷的横征暴敛。1839年林则徐禁烟,伍秉鉴虽没直接参与鸦片贸易,却和鸦片贩子往来密切,被革去顶戴关进地牢。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放弃商业利益站在清廷一边,出钱修建堡垒战船,最后还承担了110万银元的赔款。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垄断权一去不返。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832年,英国商人盗用“怡和”之名创办洋行,当时没有商标法,伍秉鉴也无可奈何。后来,英国怡和洋行成了“洋行之王”,2020年还排在世界500强第301位;而伍家的怡和行,1863年衰败后便彻底销声匿迹。两个“怡和”,两种命运,像一道隐喻,照见晚清资本的困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行纷纷搬到上海。1860年,长江流域战乱频发,中国船只动辄被抢被劫,外国船只却能畅通无阻,航运利润高得惊人。旗昌洋行联合华商买办,挂美国国旗跑长江航运,很快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用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把100万两资本金分成若干份额,出让股份,短短几个月就筹齐了钱,其中六成以上是华商附股。
旗昌的成功引来了跟风者,价格战打响,它一度陷入绝境,股价大跌。后来通过收购对手、整合市场,旗昌控制了长江60%的货运业务,还拆分股票面值方便流通,甚至涉足保险、码头,深度参与上海市政规划。

1872年,李鸿章想搞“求富”实业,盯上了被洋人垄断的航运业,筹备轮船招商局。招股说明书承诺,无论盈亏,股东每年都有一分官利,剩余利润再分红。可起初募资不顺,直到1873年,李鸿章请怡和总买办主持大局,才在半年内招得47.6万两,基本完成招股。后来,招商局竟击败旗昌,收购了它的轮船、码头和栈房,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通过竞争兼并外国企业。招商局还开辟了远洋航线,股票价格涨到近250两,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煤矿企业等多个“第一”。
好景不长,1883年中国爆发第一场现代金融危机,有人检举招商局内部挪用公款,李鸿章趁机接管,将其变回官办企业,商业竞争再次让位于政治权力。
晚清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票号和钱庄,都采用落后的无限责任合伙制。票号服务官府,钱庄贴近百姓,却都规模小、财务乱、抗风险能力差。1887年,美国商人提议创办“中美合办华美银行”,被慈禧叫停。有人后来惋惜,若当时成立这家银行,有足够资金购置军舰,甲午战争或许会是另一个结果。直到1895年,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通商银行才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则要等到1904年。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要偿还巨额赔款,只好向列强和洋行借款,连海关都抵押了出去。为了筹集民间资本,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名义上是股票,实则是公债,规定20年还清,年利5厘。可这次发行彻底失败:挤占了民族工业资本,银号钱庄纷纷倒闭;官场秩序恶化,发行成了检验官员“忠君”的标准;基层矛盾加剧,苛捐摊派屡禁不止;不少华商为避祸,改头换面变成洋商号。1898年,光绪下令停止发行,清王朝的公信力彻底崩塌。
西方国家的国债,多由专业银行和经纪人承销,在二级市场流转。而晚清缺乏专业金融机构和经纪人队伍,公债只能靠官僚机构承销,最后变成了摊派。清政府喊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建了不少军工和商办企业,却始终没建立高效的资本形成渠道,资本都耗在了官僚和军队体系里。曾经与欧洲相当的人均生活水平,在19世纪下半叶迅速下降,到19世纪末,中国成了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1/30。
欧洲的资本在制度的土壤里自由生长,晚清的资本却像被捆住手脚的旅人。资本从来不是孤立的风,它吹过的地方,既有繁荣的麦浪,也有荒芜的沙丘,而风的方向,从来由脚下的土地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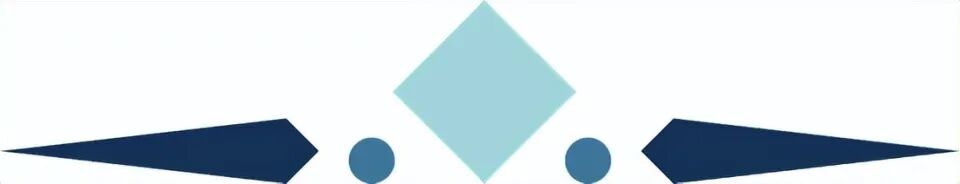
欧洲通过有限责任、股份融资、金融工具创新与法治保障,使资本有效配置于工业,推动持续增长;清末中国虽拥有庞大商业资本与"求富"愿望,但囿于官商合营、产权不明、金融落后与官僚短视,资本无法形成积累机制,最终投入无底洞的官僚军事体系,官僚阶层成为改革唯一获利者。
这里是南宫读书会,我是南宫敏羚,关注我,和我一起开启阅读之旅,每天进步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