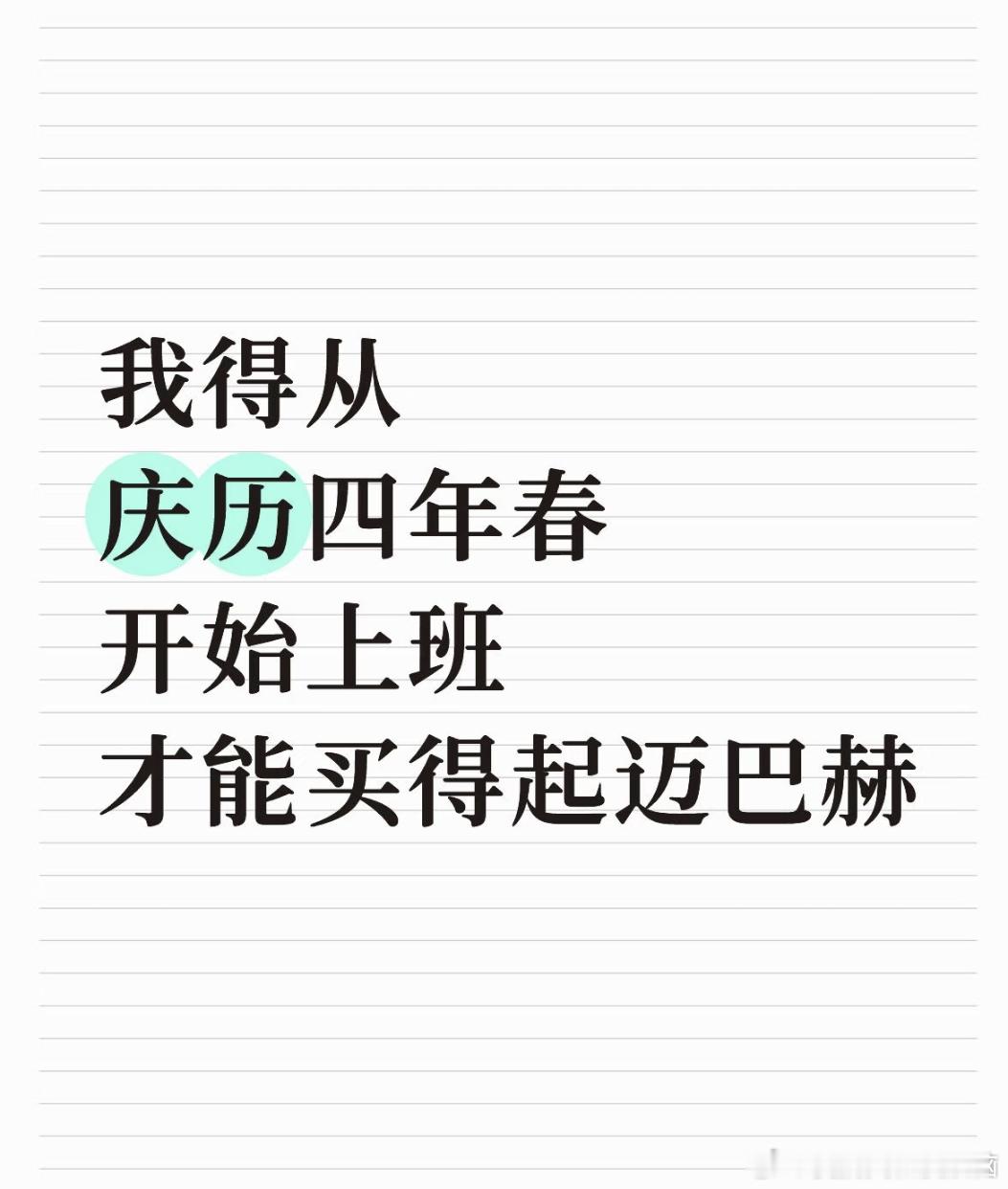河南乡下的风,腊月里带着刺骨的寒,刮在脸上像无数根细针,扎得姑娘浑身发颤。她跪在自家院门口,膝盖抵着冰冷的泥地,额头早已磕得通红,眼泪混着泥水往下淌,嘴里一遍遍哀求:“叔,求您了,让我爹安心上路吧……”

可门槛上坐着的三个男人,像三座冷冰冰的山,纹丝不动。中间是她的亲叔叔,两边是她的堂兄,三人脸上没有半分悲戚,叔叔的亲兄弟死了,不仅不帮忙,反而拦在大门口不答应让出一米宅基地就不准出殡。姑娘的父亲,这位操劳一生的庄稼汉,没能熬过这个冬天,只留下独生女和一栋老屋。
姑娘是外嫁女,却从未忘本。城里的日子再好,她总惦记着村里的老父亲,逢年过节必回,父亲生病卧床必陪。父亲走得突然,她哭红了眼,东奔西跑张罗后事,只盼着让父亲风风光光入土为安。可她万万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阻拦的,是血脉相连的亲叔叔。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老屋和宅基地,没你的份!”叔叔磕了磕烟袋,声音硬得像石头,“想让你爹出殡,先把屋后那一米宅基地让出来,给你俩堂兄分了!不然,这门你就别想跨过去!”
一米宅基地,在叔叔眼里是子孙后代的基业,在姑娘眼里,却成了刺向父亲亡灵的刀。她想不通,父亲尸骨未寒,亲叔叔怎么就能踩着棺材头抢家产?她哭着辩解:“叔,法律说女儿有继承权,这房子是我爹的遗产,我的户口还在村里,我就有权继承。”
“法律?在村里,老规矩比啥都大。”叔叔梗着脖子,唾沫星子溅在地上,“死人能跟活人争地?这地给你,你一个外嫁女能守得住?不如给你堂兄,才算留在家门里。”
村干部闻讯赶来,苦口婆心地劝:“人死为大,先让老人出殡,有事儿过后再说。”可叔叔油盐不进,坐在门槛上死活不挪窝,两个堂兄更是虎视眈眈,堵住了唯一的出路。
天一点点黑下来,寒风越来越烈,灵堂里的烛火忽明忽暗,映着父亲苍白的脸。按照乡下的规矩,灵柩不能过夜,必须在天黑前入土。姑娘看着父亲的遗体,心像被生生撕裂,她跪在地上,额头重重地磕向地面,一声比一声凄厉:“爸,女儿不孝,让您受委屈了……”
磕到额头渗血,叔叔依旧无动于衷。姑娘猛地抬起头,眼里的泪瞬间止住,只剩下被逼到绝境的决绝。她咬着牙,声音嘶哑却坚定:“砸墙!我背我爹走!”
话音刚落,围观的乡亲们都愣住了。这栋老屋,是姑娘父亲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承载了父女俩几十年的回忆。可如今,为了让父亲出殡,她只能亲手毁掉它。
几个好心的乡亲上前帮忙,找来了锤子和撬棍。“咚!咚!咚!”锤子砸在土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下都像砸在姑娘的心上。土墙并不厚实,在众人的合力下,很快砸出了一个大豁口,冷风“呼”地灌了进来,吹得灵幡剧烈晃动,也吹得姑娘的头发凌乱不堪。
姑娘扑到豁口前,看着外面泥泞的田埂,眼泪又一次汹涌而出。乡亲们小心翼翼地抬起棺材,从那个狭窄的破洞里慢慢挪出。棺材擦着墙沿,带着墙上的泥土,一点点移出了这栋被亲人隔断的老屋。
姑娘跟在后面,一手扶着棺材,一手抹着泪,脚步踉跄地踩着泥泞往前走。她一遍遍对着棺材呢喃:“爸,对不起,是女儿没用,没能让您风风光光地走……爸,您也别怪叔叔,也别怪女儿砸了您的墙,我只想让您安心上路……”

冷风卷着她的哭声,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那一米宅基地,像一道无形的鸿沟,隔断了血脉亲情,也寒透了一颗孝顺女儿的心。她不明白,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一尺一寸的土地,竟比血浓于水的亲情还重要?为什么“外嫁女”这三个字,就活该被剥夺所有权利?
棺材渐渐远去,消失在田埂的尽头。那堵被砸开的墙,像一张咧开的嘴,在寒风中无声地呜咽。它见证了一场亲情的崩塌,也记下了一个女儿为父尽孝的卑微与坚韧。而那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成了最锋利的刀,划开了人性的自私与凉薄,也刻下了一个外嫁女最深的伤痛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