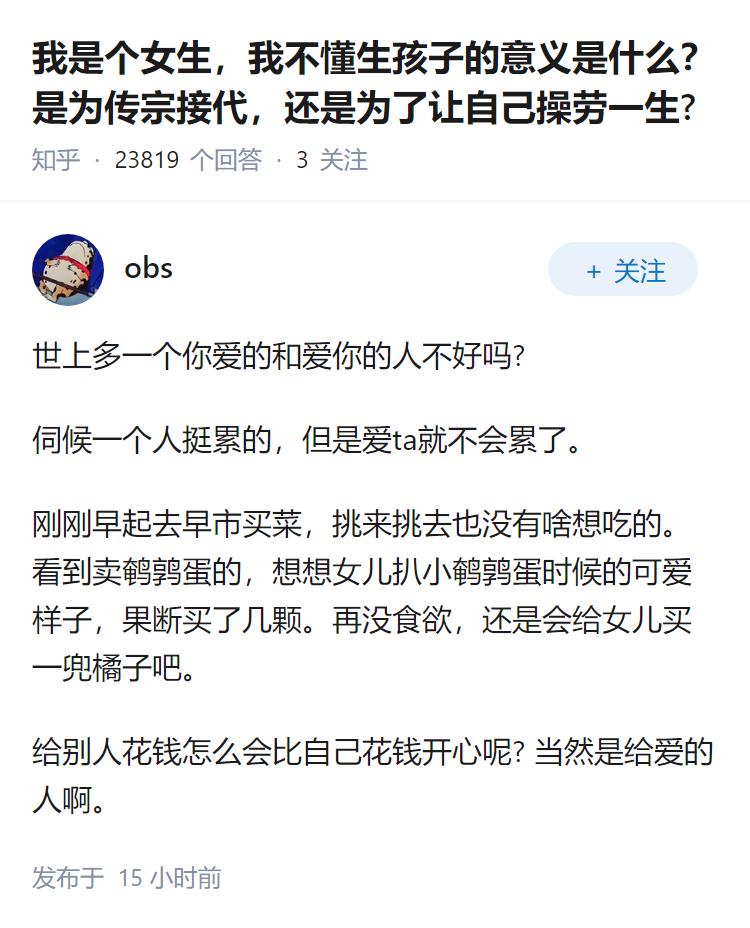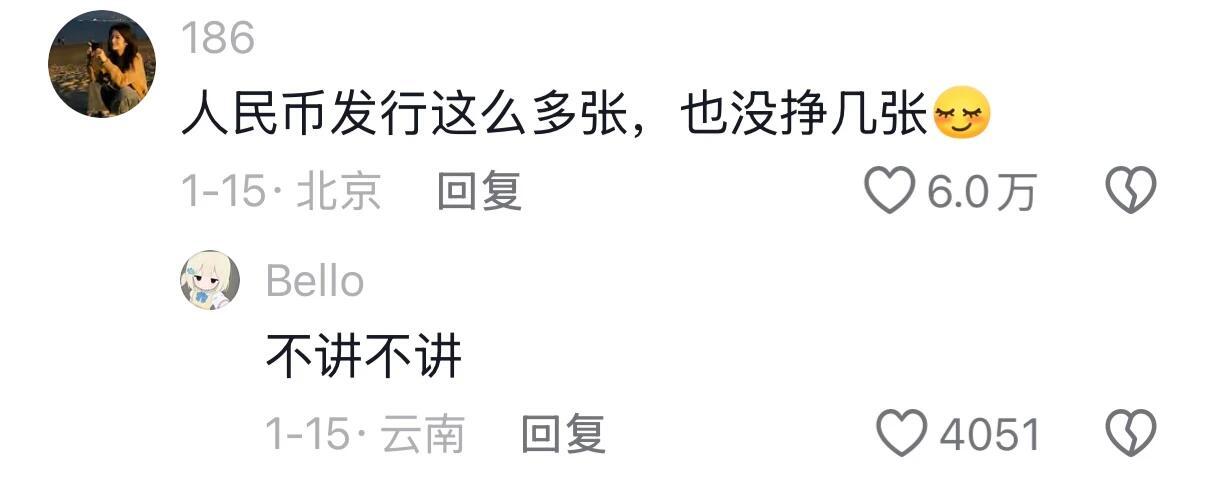陈述:雯雯
我父亲有个妹妹,就是我现在的姑姑。
两人其实并非亲生兄妹——姑姑是父亲的堂妹,是被父亲从百里外“抢”回来的。
尽管血缘的距离可能很遥远,但真正的亲情却能在最坚的阻碍面前也能一往直前地相互扑动着的温情的羽翼般的保护你。
爷爷那辈是兄弟二人。
二爷爷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留下二奶奶和一个六岁的小女儿,那就是我的堂姑。
那时的女人不像现在这样独立自由,二爷爷走后不久,二奶奶就在娘家人的安排下,带着女儿嫁到了邻县,离我们老家足有百里远。
尽管时代的局限已经将我们的选择都约束的十分的狭小,但在我们骨子里的那份深深的牵挂却终究都磨灭不了。
姑姑那时虽小,却异常懂事。
不由得想将自己留在家中和那几个伯伯、哥哥们一起生活着。
男方来接人那天,六岁的姑姑哭成了泪人,踢蹬着、挣扎着抱住门框,非要等哥哥来了才肯走。
而我父亲却被二奶奶提前支开了——家里人都知道他们兄妹感情好,姑姑就像父亲的跟屁虫,父亲有什么好东西也总先想着这个小妹妹。
所以姑姑走的那天,父亲全然不知。
二奶奶哄他说邻村有换大米的,因为姑姑爱吃大米,父亲一大早就背着小麦出了门。

孩子的直觉最纯粹,她哭的不是远行,而是被迫割舍的温暖。
等到父亲下午才回家时,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妹妹早就被他们给带走了.。
听说她哭得声嘶力竭,连一只小花鞋都踢掉了。
父亲颠倒着的一只鞋子上,抹了把滚滚的眼泪,像往常一样,又一次将我推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那时他才十六岁。
他在家沉默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一早,就背着个小包袱出了门,里面装着姑姑的两件旧衣服和那只小花鞋。
村西头老张家的两个儿子与他同行——他们在邻县有老亲,离二奶奶再嫁的人家不远。
三个少年一路走一路讨饭,五天后终于到了那个村子。
那一双小的花鞋,就像一道坚定的风信旗一样,默默地承载了少年的无数誓言和坚定的决心.。
六岁的姑姑哭肿了嗓子,二奶奶怕新婆家嫌弃,竟用布条把她捆在床头任她哭累。
父亲他们从窗外看见,三个小伙子当场落了泪。
他们要带姑姑走,二奶奶却不同意:“你一个娃娃,接回去怎么养?
她以后嫁人结婚,你能管吗?”
父亲血气方刚,拍着胸脯保证:“妹妹是王家的人,王家自然会管她。
有我这大哥在,绝不让她饿着,更不会把她捆在床上!”
二奶奶再嫁的男人也不愿留个哭闹的孩子,便顺势默许了。
有时成全不是放手,而是交给更不放手的人。
姑姑说她至今还记得,三个哥哥轮流背她回家。
饿了啃干粮,渴了找水喝。

父亲嘴甜,常向赶车人套近乎,求捎一段路。
走走停停,一周后才到家。
爷爷奶奶对姑姑回来并无异议,只是家里穷,已有四个儿子,再添一张嘴,靠爷爷每月十几元工资实在艰难。
在生活的日渐艰难背景下,父亲也早早地脱下了仕途的外袍,先后在家中开了两家小的铁铺和磨坊,后又去镇上的一家铁匠铺当了学徒,从而将家中多余的负担都卸了下来。
将深深的爱意都贮藏在了对贫瘠的岁月的无限的宽容中。
也是在铁匠铺,父亲认识了母亲。
母亲家是镇上老户,条件较好,但她却比父亲大五岁。
姥姥家看中父亲聪明肯干,才愿将女儿嫁到村里。
母亲结婚时,姥爷和舅舅请木匠在家忙了近一年,打了一套杉木柜子、樟木箱和橱子作嫁妆,在当地很是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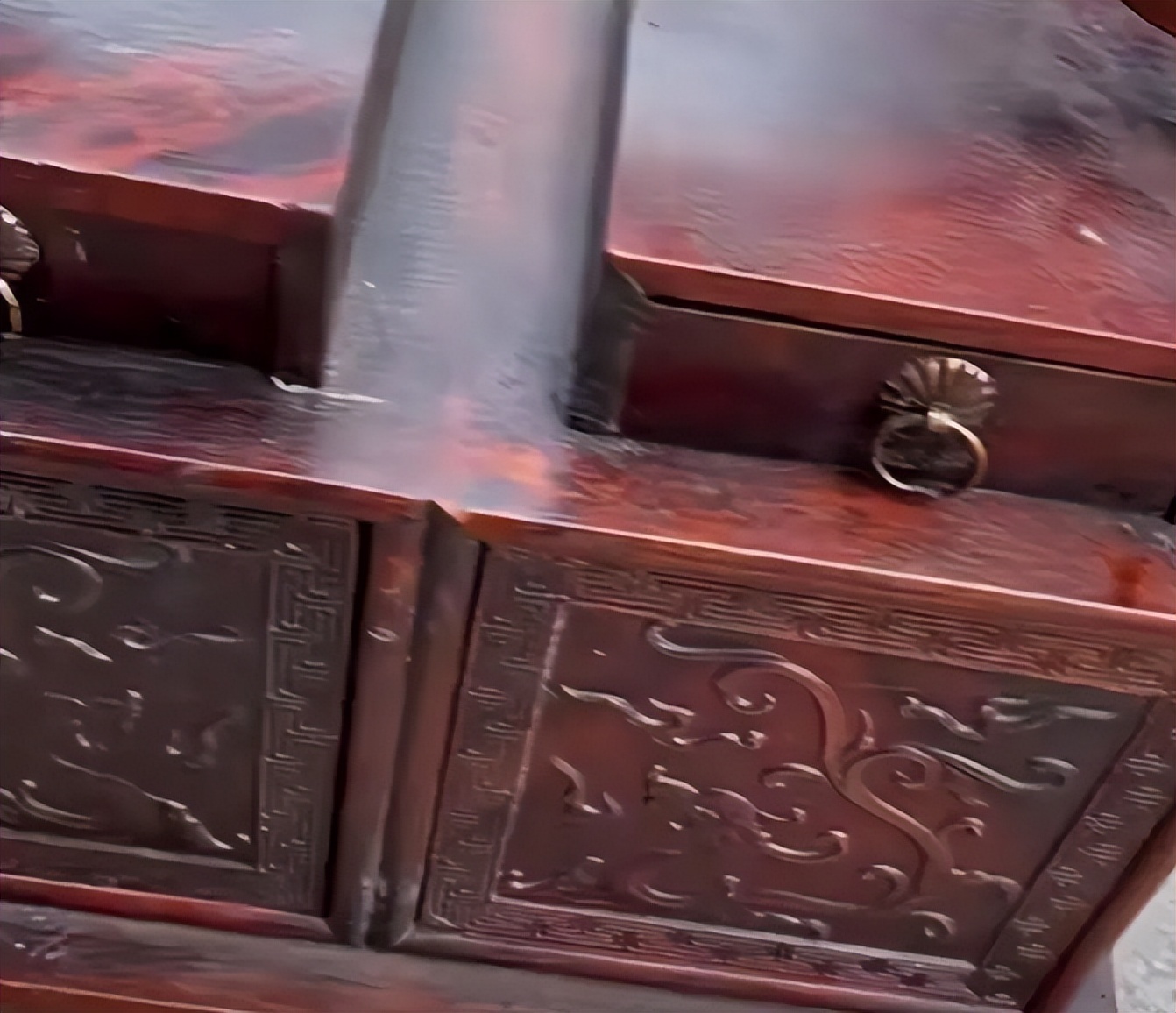
尽管婚姻的确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份既实质又温情的生活的共同体,但也常常把一份又一份的温情的爱情都当作了其结成的起点.。
婚后,在舅舅帮助下,父亲进了县水泥厂工作。
那时姑姑还在上学,母亲进门第一件事,就是为这小姑子置办新被褥送到学校。
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每月工资一发,最先留出的就是姑姑的几元生活费。
后来姑姑的婚事,也由父母一手操办。
姑父是邻村人,父母早亡,家徒四壁,亲戚们都不看好,父亲却与他深谈两次后,毅然为姑姑定下亲事。
父亲的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他对我深深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的人品和潜力都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姑姑出嫁时,父亲和三个叔叔凑钱打家具、办嫁妆,风风光光送她出门。
姑父当时在村小教书,沉稳内敛,能写会算。
工作一年多后,父亲开始为他在城里奔走。
恰逢城建局内部招人,父亲托一位同事帮忙——同事的舅舅是局里领导,而领导的妻子十分喜爱母亲那套嫁妆柜子。
思虑再三,父母咬牙将柜子送了出去。
姑父因此获得指标,进了城建局,端上了“铁饭碗”。

一件嫁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个年代的机遇往往伴随着舍弃。
姑父珍惜这份工作,勤恳努力了一辈子,退休时已是从局长位置上退下。
母亲的一套嫁妆,换来了姑父的前程,但也似乎注定了一场漫长而沉重的回报。
恩情有时是种子,在岁月里长出遮阴的树,也长出牵绊的藤。
基于父亲所在的那家水泥厂的破产,他也只能无奈地离岗谋生了。
姑姑姑父不忍看他奔波,出钱为他开了家煤厂。
煤炭的生意逐渐兴隆同时,我家也由以前的清贫渐渐走上了一条宽宽的生活之路。
那一场灾祸的降临几乎要了我的性命——就是那一夜的雨夜,我和父亲在煤厂的卸煤工作中不幸遭遇了车祸,不仅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还让我在此后的一生中都走不出一双残废的腿的痛苦中挣扎。

那时候正值我二十二岁的年华,刚步入了新人生的门槛,甚至都没来得及为自己的人生写上一道美丽的句号就被爱情的浪花推入了婚姻的海洋,而我那纯纯的妹妹还在那一本本的初中课本上痴痴地扑打着自己的青春。
家中顶梁柱倒塌,母亲一病不起。
但当那一击的命运的重击终于降临时,却常常毫无征兆,留下了无数个破碎的生活和未卜的前路。
关键时刻,是姑姑和姑父撑起了这个家。
他们安葬父亲,将母亲和妹妹接去照顾,又全力安排我的手术。
我在医院住了八个月,他们下班就奔波于医院和家中。
姑姑一年瘦了五十斤,将自家孩子托付给婆家姐姐,全心照顾我们。
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刻,才能真正体现出亲情的深厚,像春雨润物似柔情,像雪中送炭般的真挚无私。
我出院后只能坐轮椅,姑姑担心女友家反悔,便以母亲名义去商谈婚事。

不过好运气的女友也算是对我的“苦苦追求”给了最大的回报了,就这样,一个善良坚定的女孩,终于是将我从穷酸的状态中拉了出来,嫁给了我,我的生活也由此大大地改善了起了个新的人生。
婚房、彩礼等所有费用,皆由姑姑姑父承担。
但唯有经历了离去的苦难,才能清晰地在镜子般的痛楚中看到曾经的自己,也才能将留下的真心更加明晰的映照出。
如今母亲年迈,妹妹一家能力有限,已退休的姑姑姑父又将八十岁的嫂子接回家,如侍奉母亲般悉心照料。
他们常来为我做饭洗衣,我结婚二十年,每年年夜饭都由姑姑备好送来。
她总说:“只要你们过得好,我们做这些心甘情愿。”
然而,报恩和施恩的界限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一份无声的、却永远流淌不息的爱。
父母的退休生活几乎都花在了我们孩子的身上,月月的生活费都快被我们给用完了。
每次我们对自己的事情愧疚了姑姑就都会这么一说:“你爸妈当年就帮了我们这点事儿,这些钱本就该用在你们的身上了。”。”
我虽学会修手机技术,能自食其力,姑姑却总不放心:“只要我们还在,就不会不管你们。
将来我们不在了,也还有你弟弟妹妹们接着管。”
但当我们在这里的“啃老”面前却又找不到依赖的重量了,它不再是弱者的一种可耻的依赖,而是一种被他人坚定地接住的坠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被他人有意无意地给予的生存的托起。
这些年来,我们两代人都在接受姑姑一家的付出。
当年母亲那份嫁妆的情谊,他们用一生甚至两生来偿还。
二十年的轮椅生活中,我几乎每三天就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无论大雪封路他们也总要亲自来一次看一看才能心安理得地走开。

只有将爱浸润到生活的每一刻,每一个细节中,爱才会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像空气一样的不可或缺,稍有不舍都会让人感到一丝的不适。
但愿能以最真挚的感恩之情,用一生都不能偿还的汗水与心力,来回报您的这份恩情.。
只有通过将这段缠绵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一一地将之写下,让这份从跨越了血缘的隔阂、历经了两代人的守护之情都用文字来承载,才能让它的真谛在时间的长河中一一地被人所感同身受,才更让这份情感的深深的流淌更为真切。
有些债永远还不清,因为它本就不是债——那是心甘情愿的循环,是家族血脉里流淌的、无需言说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