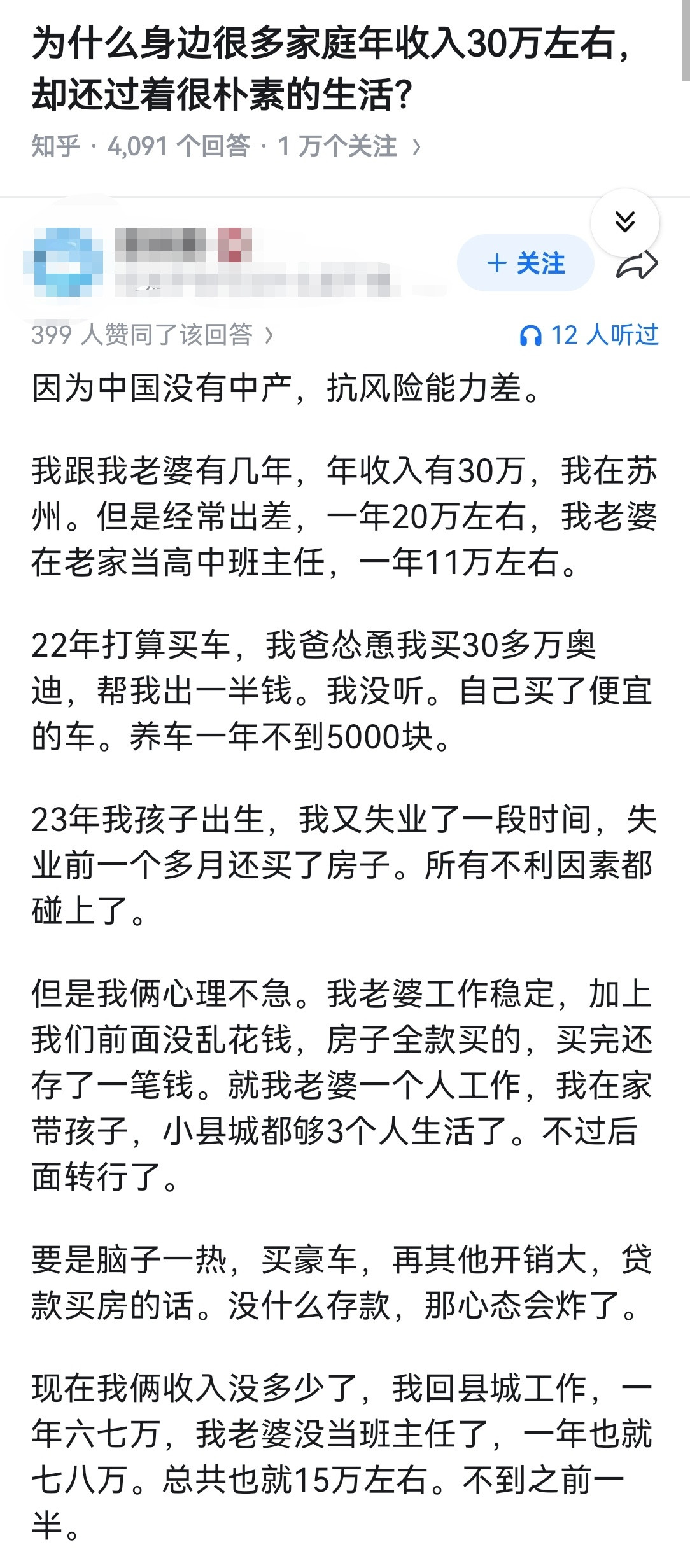老山一等功臣陈之耕烈士,1964年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洛河镇屯头村一农民家庭,1984年1月入伍,83012部队一团七连机枪手。 1984年7月,陈之耕随部队赴云南前线,参加对越作战。 那年夏天,闷罐列车咣当咣当往南开,车厢里挤满了和陈之耕一样年轻的士兵。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那么远,不知道前线具体在哪儿,只晓得是去打仗。火车越往南,窗外的山越密,绿色浓得化不开。陈之耕怀里抱着那挺56式班用机枪,枪身冰凉,手心却一直在出汗。他才二十岁,四个月前还在家乡的田埂上走着,现在肩上扛着的是全班最重要的火力。 老山那个地方,地图上只是个小点,真正到了才知道什么叫“绞肉机”。山高林密,雾大得对面看不见人,亚热带的雨说下就下,战壕里积水能没过膝盖。最要命的是满山的地雷和躲在暗处的冷枪,每往前挪一步,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陈之耕所在的七连,负责进攻的一个重要高地。越军的火力点藏在天然岩洞里,机枪交叉封锁,压得突击队抬不起头。 就是在那样的绝境下,陈之耕做了选择。战友回忆,当时他喊了句“我吸引火力!”,就抱着机枪从侧翼猛地跃出,一边冲锋一边朝着敌火力点猛烈扫射。敌人的子弹瞬间集中朝他招呼,打在身边的岩石上溅起一片火星。他硬是凭着一股不要命的劲头,成功突进到离敌人工事不到三十米的地方,用机枪和手榴弹药,端掉了那个最致命的火力点。突击通道打开了,可他也在完成任务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 后来战报上写的是“一等功”,写的是“英勇无畏”。可真正了解那场战斗的老兵会说,战场上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被逼到绝境的普通人。陈之耕做出那个决定可能就几秒钟,支撑那几秒钟的,是四个月新兵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是身边倒下的战友,更是一种最朴素的责任——“我是机枪手,我不上谁上?”他不是不知道危险,只是在那个关头,个人的生死被更重要的东西压过去了。 我曾在云南的烈士陵园见过类似的墓碑,密密麻麻,几乎望不到边。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和陈之耕差不多的故事:年轻,来自某个普通的村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永远定格在了南疆的焦土上。我们这代人离战争太远了,远到很多人已经无法想象,当年那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是如何在泥泞、恐惧和血腥中,完成那些被称为“英勇”的壮举。他们不是史诗里刀枪不入的神,是会害怕、会想家、受伤了会疼的普通人。正因如此,他们的选择才格外沉重,也格外真实。 有人说,战争是政治的最后手段。这话没错,但真正承受这“最后手段”全部重量的,永远是千千万万个具体的“陈之耕”。他们的牺牲,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这是大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每一个牺牲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崩塌。安徽淮南那个叫屯头村的地方,有一对农民父母永远失去了他们刚满二十岁的儿子。国家的功臣,同时也是父母心头无法愈合的伤疤。理解这种双重性,我们才能更完整地看待英雄。 这些年,总有一些声音,试图用轻佻的态度解构历史,甚至质疑那场边境战争的必要性。这种论调,不仅是对无数烈士英灵的亵渎,更是对历史的无知。战争从来不是选择题,当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主权和领土完整被侵犯时,自卫反击是唯一的选择。陈之耕和他的战友们,用生命捍卫的,正是我们今天得以和平发展的底线。忘记他们,就意味着背叛。 陈之耕牺牲后,被安葬在云南的烈士陵园。他的故事,和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一样,渐渐沉淀在档案里,沉淀在亲人不愿轻易触碰的记忆深处。这是历史的常态,时间会冲淡很多东西。但一个民族的精神谱系,正是由这些看似遥远的名字和故事编织而成的。他们像基石,沉默地托举着我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我们纪念陈之耕,不只是回顾一场战斗。更是要思考,在和平年代,如何传承那种最纯粹的责任与担当。这种担当,不一定非要体现在战场上。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在诱惑面前守住底线,这些都是英雄精神在平凡生活中的延续。让“陈之耕”们不被遗忘,最好的方式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让我们自己,活成一个有责任感、有血性的人。 南疆的木棉树,年年花开如火。那红色,像极了当年阵地上年轻的鲜血,也像今天宁静岁月里,我们心头不该熄灭的火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