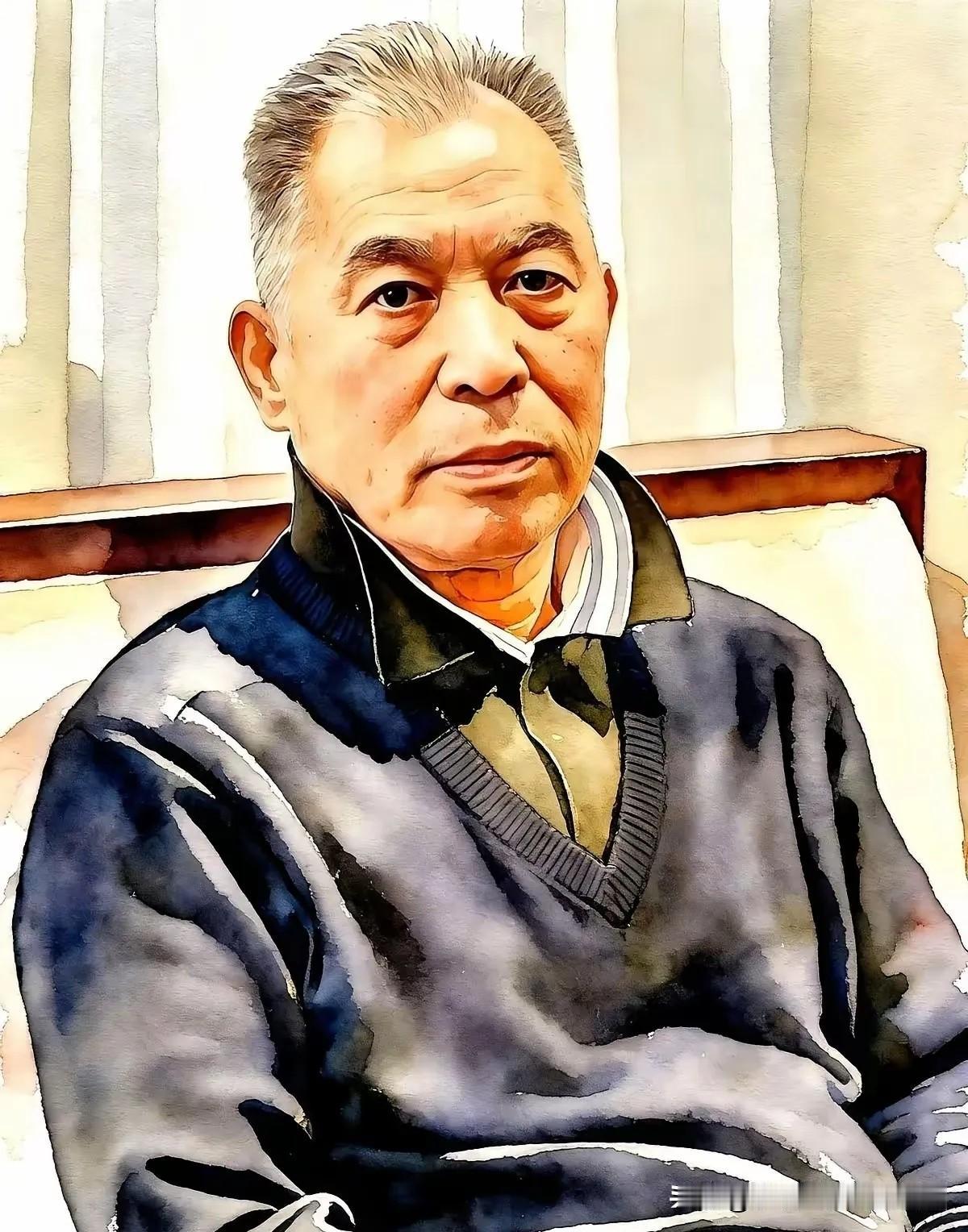父亲走,和母亲走,是两回事。 我爸走那年,家里顶梁柱塌了。但过年,年夜饭的桌子照样摆得满满当当。 我爸走在深秋,刚收完玉米,院里的晒场还堆着没清的秸秆。母亲把自己关在厢房哭了半宿,第二天红着眼圈爬起来,翻出父亲生前用的竹篮,踩着晨霜去赶集。她买回来五花肉、带鱼、活鸡,还有我爸最爱的酱肘子,满满当当堆了一案板。 那时候我刚上高二,放学回家总看见母亲坐在灶台前,火钳夹着柴火往灶膛里送,火苗映着她的脸,皱纹比以前深了好多,却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叹过一声气。 除夕那天,她凌晨四点就起了床,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声响把我吵醒,推开门看见她正站在锅前焯排骨,蒸汽裹着肉香漫出来,她的袖口卷到胳膊肘,手腕上的银镯子晃来晃去,那是我爸年轻时给她打的。 那天的年夜饭,桌子真的摆满了。糖醋鱼炸得金黄,红烧肉炖得脱骨,就连我不爱吃的藕夹,母亲都做了满满一盘。弟弟忍不住伸手去捏一块排骨,被母亲轻轻拍了下手背:“等你姐和你哥回来再动筷。 ”大哥从外地赶回来,进门就去厨房帮衬,母亲却把他往外推:“你歇着,你爸不在,我得把这顿饭做好。” 开饭时,母亲把酱肘子摆在桌子正中央,给每个人碗里都夹了一块,自己却没动筷子,只是端着一杯白开水,看着我们吃,眼角亮晶晶的,嘴里念叨着:“你爸要是在,肯定要喝两盅。 ”那天的饭,大家吃得很安静,却没人放下筷子,母亲夹过来的菜,我们都逼着自己多吃两口——我们都知道,她是在硬撑,撑着让这个家看起来和以前没两样。 母亲走在开春,桃花刚打骨朵。她走得突然,脑梗发作,没留下一句话。那年除夕,我和大哥、弟弟照着母亲生前的样子,去菜市场采购。 我站在肉摊前,老板问要多少五花肉,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以前都是母亲报斤两,说“要三斤,瘦点的,炖红烧肉”,现在我连该买多少都不知道。 回到家,厨房空荡荡的,灶台上落了层薄灰,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生火,柴火却总也点不着,烟呛得我眼泪直流。 大哥在旁边切菜,菜刀剁在案板上,咚咚的声响显得格外冷清,他切的土豆丝粗细不一,不像母亲切的那样匀整。弟弟想炸带鱼,油烧得冒烟,他把鱼一放进去,油星子溅出来,烫得他直跺脚,最后带鱼炸得焦黑,根本没法吃。 那天的年夜饭,桌子上也摆了七八道菜,却怎么看都透着寒酸。没有炖得软烂的红烧肉,没有外酥里嫩的糖醋鱼,就连母亲最拿手的八宝饭,也因为我放多了糖,甜得发腻。我们三个坐在桌前,谁都没怎么动筷。 大哥拿起酒杯,倒了三杯酒,一杯洒在地上,嘴里低声说:“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弟弟突然哭了,说:“姐,我想吃妈做的藕夹。”我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原来父亲走了,母亲还在,家就还有个模样;母亲走了,才是真的散了半壁江山。 我想起小时候,年夜饭的桌子底下,母亲总在给我们剥橘子,父亲坐在主位,给我们讲他年轻时跑运输的趣事。那时候的屋子不大,却挤得满满当当,暖气烧得足,空气里都是菜香和笑声。 我爸走后,母亲把他的照片摆在客厅正中,过年时会给他摆上一双碗筷,说“老陈,过来吃年夜饭了”;母亲走后,那张照片旁边,又多了她的相框,两只相框并排摆着,看着我们三个手足无措地摆弄着一桌饭菜,却再也没人给我们剥橘子,没人叮嘱我们“慢点吃,别噎着”。 后来我才慢慢懂,父亲是家的骨架,撑着屋顶,挡着风雨,他在,我们就有安全感;母亲是家的血肉,填着烟火气,暖着人心,她在,我们就有归属感。 父亲走了,骨架还能靠着彼此支撑;母亲走了,血肉没了,剩下的骨架再硬,也觉得空落落的。年夜饭的桌子能不能摆满,从来不是看有没有钱买食材,而是看有没有那个愿意为你熬夜备菜、愿意强撑着悲伤也要让你吃好的人。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亲的离开让我们学会坚强,母亲的离去却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家,从来不是一栋房子,而是父母在时的热饭热菜,是他们唠叨里的牵挂。 那些曾经觉得平淡的日子,如今想来,全是再也回不去的幸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