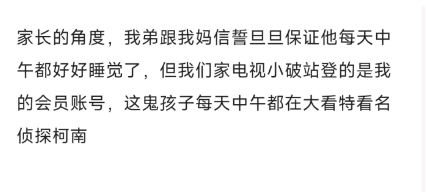自从爷爷奶奶去世后。两个姑姑和我们都没有联系了,过年过节也没有问候,就像断了亲情一样。最后一次见到大姑和二姑,是奶奶出殡那天。大姑抱着奶奶的遗像哭倒在灵前,二姑红着眼圈给前来吊唁的人鞠躬,我爸蹲在墙角抽着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 奶奶走后,家里的年就空了。 姑姑们像两滴融进大海的雨, 再也没在我们的生活里泛起过涟漪。 最后那次见大姑二姑,灵堂白幡飘着, 我爸蹲在墙角抽烟,烟灰吊在半空,像根没说完的话。 大姑抱着奶奶的遗像哭到背过气, 孝服前襟全湿透了, 二姑红着眼圈给吊唁的人鞠躬,指尖攥得发白。 那天天很阴,送葬队伍把路压得沉沉的, 我回头望,看见二姑偷偷往我爸手里塞了个红包, 他没接,手垂在裤缝边,像截枯树枝。 去年清明我试着发微信给二姑, 问她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奶奶。 对话框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转了三圈,跳出一句:"你爸……还好吗?" 我盯着屏幕突然鼻子发酸, 原来有些结,不是解不开,是没人敢先伸手。 其实谁都没说过"断交"两个字。 就像老座钟的摆突然停了, 不是齿轮坏了,是没人记得上弦。 以前奶奶在,是她把我们串在一根线上的。 她喊吃饭,姑姑们就提着点心匣子来了; 她骂我爸抽烟,大姑会跟着数落,二姑就默默把烟盒收起来。 现在线断了,谁都不知道该先伸手去接哪一头。 我妈说姑姑们是怪我们没照顾好老人, 可那天灵前,大姑哭着喊"我的妈呀", 那声音里的疼,不像是装的。 或许成年人的告别就是这样, 不说再见,只是再也不见, 把委屈和想念都腌在心底,等时间发酵成沉默。 上个月整理奶奶遗物, 翻出个铁皮饼干盒,里面是姑姑们年轻时给她织的毛袜, 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串没对齐的省略号。 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大姑,配文:"奶奶还留着这些呢。" 这次她秒回了个流泪的表情, 后面跟着一句:"你爸胃不好,让他少喝浓茶。" 血缘这东西真奇怪, 像埋在地下的树根,平时看不见,下点雨就冒出新的绿芽。 或许我该再发条微信,不说探望, 就问"姑姑,你还记得奶奶腌的萝卜干怎么晒吗?" 窗外的玉兰开了,我爸坐在阳台抽烟, 打火机"咔嗒"一声,烟圈悠悠地飘向对面楼—— 那里住着二姑,只是我们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