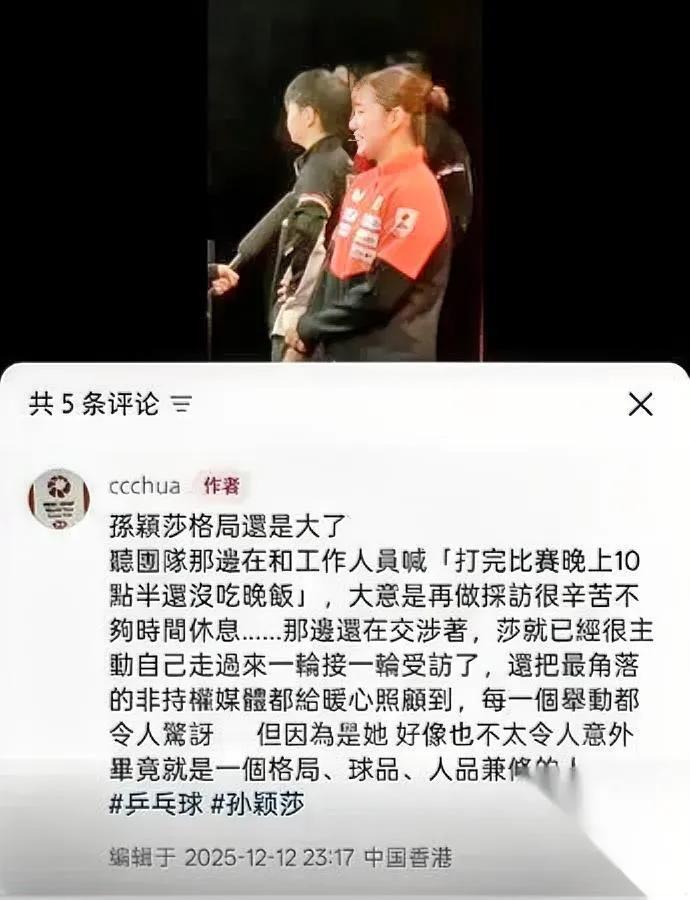今天,母亲在我面前呻吟的时候,我选择了装糊涂。不是我不孝顺,是我发现我越来越孝顺不起来了。当时我正坐在客厅里改方案,母亲从房间里出来,扶着腰,一边慢慢走到沙发边坐下,一边嘴里“哎哟哎哟”地哼着,手还不停地揉着腰。 改方案的键盘声敲得我太阳穴突突跳,客厅的老挂钟滴答滴答,像在数我和母亲之间的沉默。沙发扶手上那个格子靠垫磨得边都卷了,是她去年缝的,说坐着腰能舒服点——可现在她正用手死死按着腰侧,指节发白,哼唧声从喉咙缝里挤出来,像漏风的风箱。 她从房间出来时,我眼角余光扫到了:右手扶着墙,左手撑着腰,一步一挪,拖鞋在地板上蹭出“沙沙”的响。我赶紧把视线钉回电脑屏幕,文档里的“优化方案”四个字突然变得模糊,手指却机械地敲着回车,假装在调整格式。 “哎哟……”她终于挪到沙发边,慢慢坐下时,哼唧声大了点,“这老腰,真是越来越不听使唤了。” 我没接话。键盘声敲得更响,好像这样就能把那声音盖过去。她开始揉腰,一下,两下,袖口滑下来,露出手腕上那块淡褐色的老年斑——去年这时还没有的,或者说,我去年根本没注意过。 “你忙不忙啊?”她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像含着口水。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算设问吗?算吧,她明明看见我对着电脑皱着眉。 “忙,妈,”我盯着屏幕上的进度条,“甲方催下午交初稿,急得很。”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哼唧声停了,只有揉腰的动作还在继续,一下,两下,慢得像在数时间。我突然想起十岁那年,我半夜摔下床崴了脚,也是这样哼哼唧唧,她抱着我坐在这张沙发上,拿热毛巾给我敷,敷完又给我揉,揉到我睡着,第二天早上她眼睛都是肿的。那时候她怎么就不嫌我吵呢? 也许她不是真的痛得受不了?我偷偷抬眼,看见她盯着茶几上我昨天没喝完的半杯豆浆,杯子壁上结了层奶皮。她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待久了,闷得慌,想找个由头跟我说说话?又或者,是我最近太不像话了——连续三周加班,上周六她生日,我都说“项目忙走不开”,最后只在美团上订了个蛋糕。 我改方案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个项目奖金,想着下个月发了工资,就给她换个带按摩功能的床垫,她总说睡硬床腰不舒服。可现在呢?她就坐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用最笨拙的方式喊我,我却躲在“忙”这个壳里,连头都没抬一下。她大概是觉得,我长大了,翅膀硬了,不需要她了——就像她现在,也不好意思再像小时候那样,直接说“妈想你陪我说说话”。 过了十几分钟,她慢慢站起来,扶着沙发扶手,没再哼唧,也没看我,一步一挪地走回房间。关门声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我盯着电脑屏幕,文档还停留在“优化方案”那一页,可一个字也改不进去了。 刚才要是问一句“妈你要不要贴个膏药”,很难吗?或者哪怕只是抬头看她一眼,说“等我忙完这阵带你去医院看看”,她会不会就不那么落寞了? 天黑透的时候,方案终于改完了。我关掉电脑,客厅里静得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门缝里透出一条暖黄的光。我起身去厨房倒水,路过沙发时,看见她刚才坐的地方,留着一片小小的阴影——是她忘在那里的护腰贴,包装上印着“发热型”,和去年冬天她给我买的那个牌子一模一样,当时我总说办公室空调冷,腰受凉疼。 我拿起那片护腰贴,手指触到包装纸,有点凉。也许明天早上,我该早点起,煮碗热粥,然后问她:“妈,今天要不要一起去公园走走?听说那边的桂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