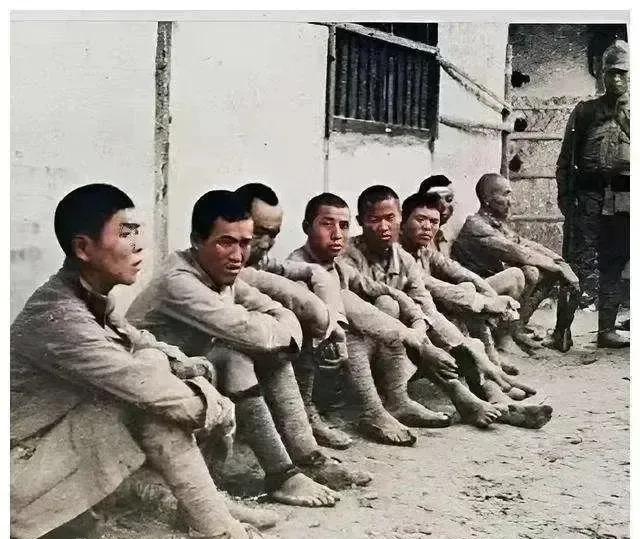1889年,张作霖的爹被人谋杀了,张作霖却还在玩骰子。母亲让张作霖去县衙门报官,不料,张作霖却摆摆手说:“不去!我这亲爹,不要也罢!”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走到没人的地方,他却突然狂奔起来。 那年奉天的秋老虎正烈,14岁的张作霖蹲在营口附近的赌场角落,粗瓷碗里的骰子转得咔嗒响。母亲的哭声像根针戳破嘈杂,他却盯着碗底那粒嵌进裂纹的骰子——父亲张有财三天前还在这里赢了钱,说要送他去私塾的。 消息是邻村货郎偷偷递来的:王连仲的人在回村的土路上动了手,尸体扔在乱葬岗。母亲抹着泪要往县衙跑,张作霖却拽住哥哥张作孚的袖口,眼神扫过赌场墙角那堆没人要的驴粪——那是他们约好的记号。 兄弟俩摸到村外废弃的驴棚时,草垛里的土猎枪还带着铁锈味。这杆枪是用张作霖赢的两个铜板,加上张作孚偷藏的压岁钱,托铁匠铺的远房表舅打的。棚顶漏下的月光,把枪托照得像块浸了水的木头。 深夜翻墙时,张作霖蹲在墙根当垫脚石,张作孚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枪托撞在砖墙上闷响一声。谁也没料到,第一个推门出来的不是王连仲,是起夜的老太太——黑暗里她的惊叫声像只被踩住的猫。 枪声在寂静的村子里炸开时,张作霖正往墙上递第二块石头。他看见哥哥举着枪僵在院里,家丁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火光照亮张作孚脸上的血——不知是自己的还是老太太的。 他没有喊,也没有冲进去,转身就往乱葬岗的方向跑。鞋跑丢了一只,脚心被碎石子划得火辣辣疼,可他不敢停——身后的狗吠声越来越近,像要把这14岁少年的影子撕碎在秋夜里。 村里人都说张家小子心狠,亲爹死了还赌钱;母亲哭了三天,以为两个儿子都废了。只有张作霖知道,那天在驴棚里,他往枪膛里塞火药时,手稳得像个常年使枪的猎户——有些事,哭没用,告官更没用。 那时的奉天乡下,县太爷的轿子半年才来一次,来了也是收完银子就走。张有财赢的那点钱,不够买通衙役的一顿酒;王连仲家的地租却能让半个村子的人闭嘴。或许正是这种叫天天不应的日子,把“靠自己”三个字,早早刻进了张作霖的骨头里。 张作孚后来判了十年刑,张作霖成了闯关东的流民。他在营口码头扛过包,在蒙古草原放过马,挨过饿也挨过打,可每次摸到腰间那把磨得发亮的匕首,就想起驴棚里那杆生锈的猎枪。 多年后他在奉天城当上巡防营统领,办公室墙上挂着幅《寒江独钓图》。有下属问他喜欢钓鱼?他笑了笑没说话,指尖划过画中渔翁的钓竿——那弧度,和当年他蹲在墙根当垫脚石时,脊背弯的弧度,一模一样。 如果那天他跟着母亲去报官了呢?如果张作孚没有误杀老太太呢?历史没有如果。但那个在没人处突然狂奔的少年,早已把“隐忍”和“决断”,酿成了闯荡乱世的酒——烈,却能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