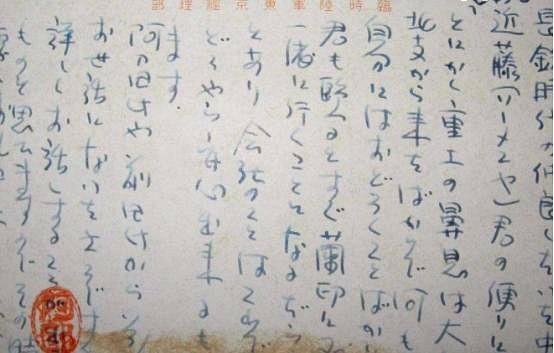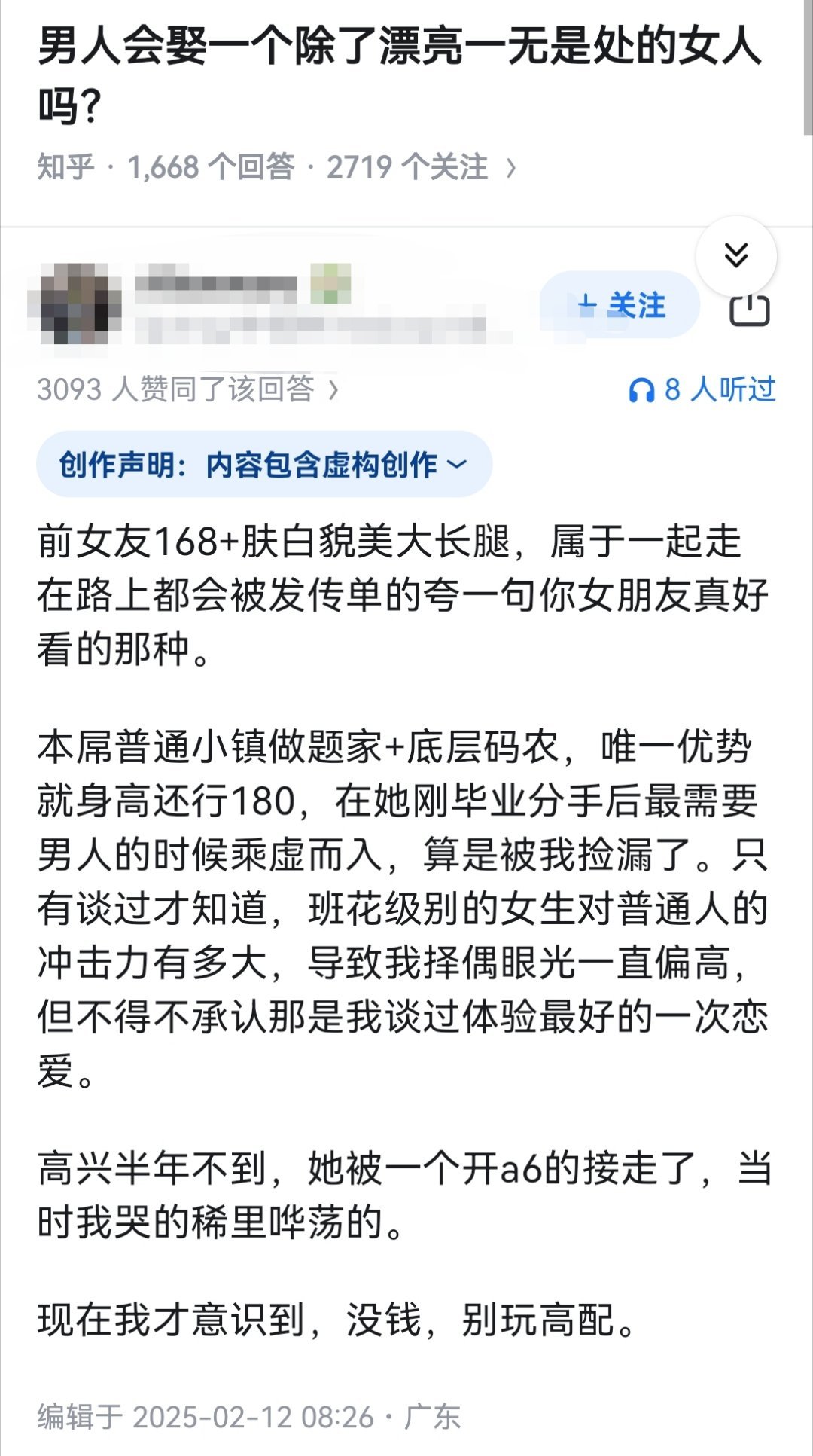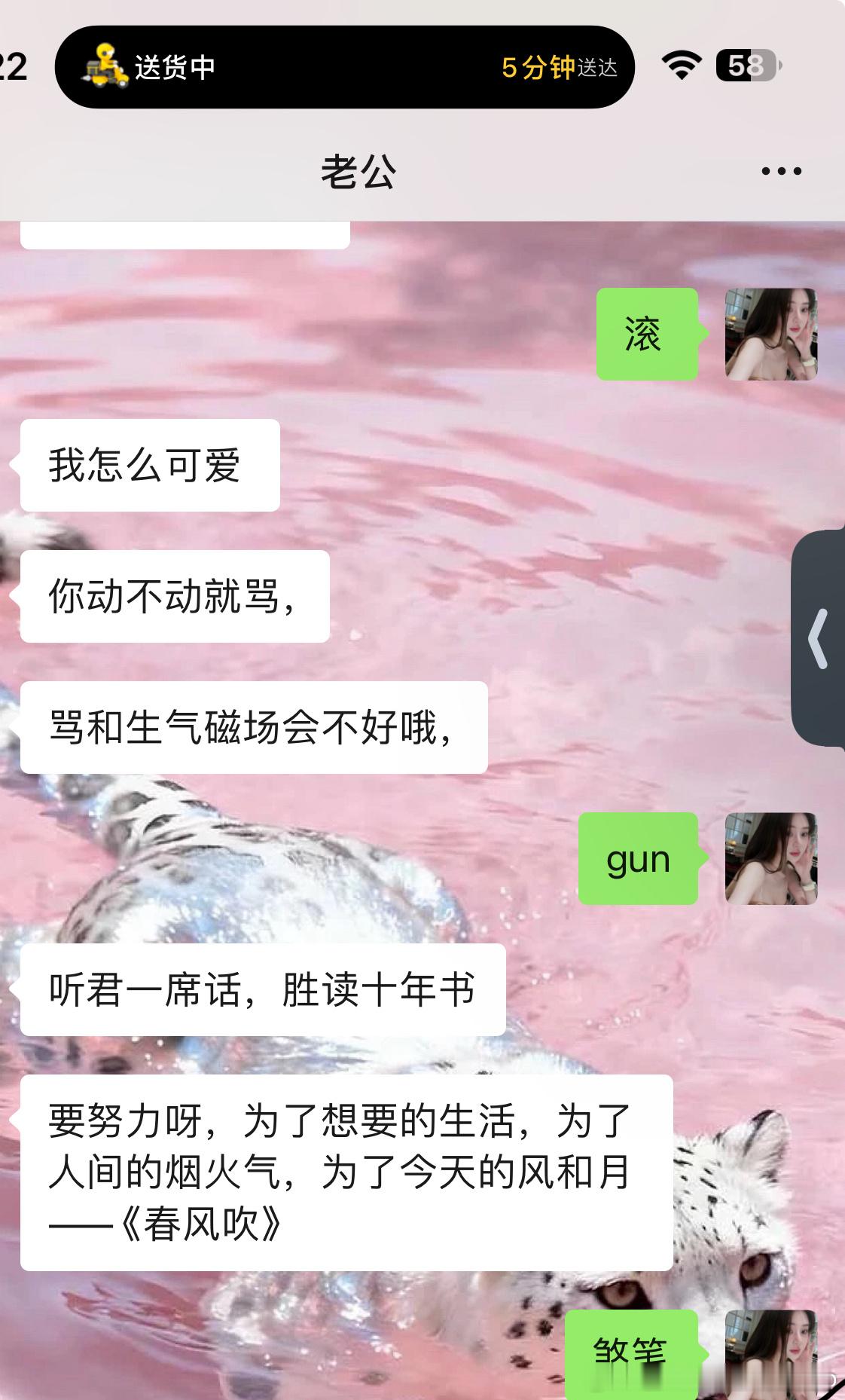婉容最后是活活臭死的。大小便失禁,躺在自己的屎尿里,浑身烂疮,41岁的女人,瘦得像一具骷髅。 谁能想到,这具连狱卒经过都要捂鼻快走的躯体,曾是那个在长春御花园里,让樱花都失色的婉容皇后? 她记得樱花飘落时,自己穿着绣凤的旗袍,裙摆扫过光洁的金砖地,宫女们垂手立在两侧,连呼吸都放轻了。 枯瘦的指节死死嵌进烟枪的象牙纹路里,那上面刻着的“婉容”二字早已被污垢糊住,却被她摩挲得发亮。 霉味混着脓水的腥气,像层黏腻的薄膜,裹住四壁,也裹住她蜷缩的身子——曾经擦着法国香水的脖颈,如今只剩溃烂的创口在渗液。 送饭的狱卒经过铁栏,总会把木碗重重摔在地上,仿佛多看一眼,那股恶臭就会钻进骨头缝里。 粗布囚服烂得像破渔网,露出的皮肤上,旧痂叠着新脓,青紫色的淤痕从手腕蔓延到锁骨,像条丑陋的蛇。 她想起梳妆台上的螺钿镜,镜里的自己有杏核眼、柳叶眉,指尖蘸着玫瑰膏,轻轻点在唇上。 突然一阵剧烈的痉挛扯着她的胃,她像只被踩住的蚂蚱,蜷缩得更紧,喉咙里挤出细碎的呻吟,很快被死寂吞掉。 烟瘾上来时最是难熬,她会拼命把烟枪怼到唇边,舌尖徒劳地舔着冰冷的枪头,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烟管早空了,可她偏要做这个梦,梦见烟泡在灯上滋滋作响,白雾裹着她飘回长春。 身下的稻草早成了灰,和屎尿混在一起,结成硬壳粘在背上,一动就是钻心的疼,可她连抬手掀开的力气都没有。 天光暗透时,她的手突然松了松,又猛地攥紧——那根烟枪终究没离手。 曾经让她俯瞰众生的凤冠早已不知所踪,只剩这根象牙烟枪,陪着她在臭水沟般的牢房里,咽下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