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文字整理:季风
对话嘉宾:冯北仲(学者、作家)邓琪(宁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冯北仲/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冯北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陕西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嘉宾简介
冯北仲,哲学硕士,陕西泾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陕西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先后入选陕西省首批、二批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资助计划。出版长篇小说《遗园》《看不见的力量》,小说集《卡夫卡的妄想》。近年来,在《文艺报》《芳草》《长城》《延河》《雨花》《鸭绿江》《广州文艺》《时代文学》《黄河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遗园》先后获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汉中市首届“五个一工程”奖;《看不见的力量》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4年第四季度影响力图书“文学类”榜单;《卡夫卡的妄想》入选2025年9月百道好书榜“文学类”榜单。
邓琪,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在《朔方》《百花》《南腔北调》《民族艺林》《六盘山》《宁夏日报》《宁夏文艺家》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数篇。部分文章被中国文艺评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西大创意写作中心等平台转载或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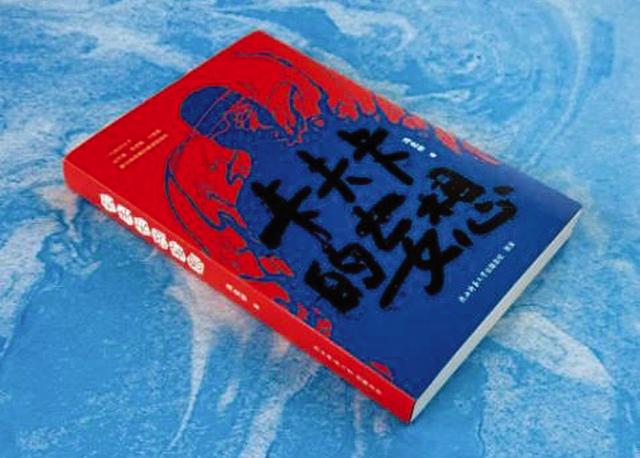
冯北仲作品《卡夫卡的妄想》。

冯北仲作品《看不见的力量》。

冯北仲作品《遗园》。

作家冯北仲在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颁奖典礼上。
邓琪:冯老师,您好!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您的中篇小说集《卡夫卡的妄想》一经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并入选2025年9月百道好书榜“文学类”榜单。可以就您新近推出的这本小说集,谈一谈创作时的艺术构思和深刻体会吗?
冯北仲:我发表短中篇小说始于2015年,到2025年恰好整整十年。《卡夫卡的妄想》收录了描写知识分子的六部中篇小说,相当于串起了十年时间中的六颗珠子,闪烁着各自的光芒和风姿。光芒是小说的思想,风姿是小说的艺术。也就是说,每颗珠子串起了不同的艺术构思。六部小说中,描写了不同的人物,人物的不同境遇,境遇下不同人生的起伏与磨难,一个个的“他们”绘制出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共振的十年旅程——心理状况和精神危机。所以,就艺术构思来说,六部小说创作时间不同,因人物自身的多种差异决定了叙事方式的不同,却也有共同点。简言之,共同点即是“三一律”:“一”是小说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一”是描写了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一”是小说里,在“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中努力展示有别于其他几部的独特性。小说集子,与长篇小说不同。艺术构思是一项复杂的课题,既独立成篇,又有内在关联,因相同而具有连续性,因不同又具有独特性。《卡夫卡的妄想》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拿到书后,我心情比较复杂。写作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一旦进入旅行轨道,没有回头路,注定只能朝前走。十年看似一个阶段的总结,也预示下一个“新十年”的开始。实质上,十年的真正内涵和意义,不在于一个“时间过程”。若是一个写作者显摆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概念,那写作本身没有太大价值。显摆的最大弊端,是隐藏了事实的内核,“内核”是一个无限逼近事物本质的概念,而“本质”恰是庸常思维最易忽略的。写作的本质,不是证明写了多少篇,而是证明写作者的思考程度。这正是哲学上的“一与多”的关系,重复在“多”篇,没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突破,没有体现出独特性,本质也是“一”篇。作品不在于“多”,而在于别致的“一”,也就是作品在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时间性重在显示“时间”的内涵层次,恰好是考量写作旅行的“尺度”,不是物理学上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以“分量”体现一段写作历程的真正意义。
邓琪:这本小说集一共收录了您近年创作的六部中篇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张柠教授评价说:“《卡夫卡的妄想》向我们宣告,卡夫卡不再是我们遥望和揣摩的对象,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冯北仲将布拉格的表现主义,改写成长安的现实主义。”您的作品让卡夫卡从“遥望的对象”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从“布拉格”来到了“长安”。那么,当读者视您为“长安的卡夫卡”或“中国的卡夫卡”时,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文学道路与前人前作的关系?
冯北仲:人类社会在原始初期,就有了审美,确切地讲既有美的追求和向往,也有了美的表达。当然,那是感性的、朴素的审美,是人类在童年无意识的文学时期。所以说人类自诞生起,天生就带有文学的神奇基因。中西文学发展初期,成长脚步几乎同频,童年时代都经历了神话。相较来说,西方的神话体系较为完整。中国神话侧重人文道德,西方神话则更多展现了天真烂漫、戏剧性和体系化的叙事性。中西文学之所以有差异,源于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和表达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后世各自发展的路径。但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题材之间也有交叉和重合。文学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基因,具有精灵的特质,自带光芒和超越性,不分国度和民族,更没有优劣之分(作品是有优劣之分的)。文学是人类共有的天然基因,人类发展史上,中西文学不断对话和会通,相互彰显优长和特色,彼此不断融合。表现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从事文学创作,也是学者(法学博士)。他没有成为一名好律师,而是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充满兴趣,更是视尼采为他的精神导师,成了一代文学大师。古今中外,每一个优秀作家的成长,都是在先辈们的脚印里探求自己的方向,都是“作家中的作家”——这是优秀作家必走之路。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西方文学谱系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吸收和承接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精华。《变形记》的名字不是卡夫卡的首创。他学识渊博,文化底蕴深厚,借鉴和吸纳了奥维德《变形记》,并且结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语境和自身处境,经过艺术虚构和想象,将古罗马的《变形记》写成了布拉格的《变形记》。卡夫卡属于全人类,不仅仅是布拉格。他属于世界文学,也属于地球上所有的作家。“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吸收西方文化,西方也吸纳中国文化。至今,世界文化已是共同起舞,汹涌地汇入人类历史的洪流。中西文学更是不断碰撞,深入融合,丰富且繁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我是一名作家,我用笔写我心;我的文章展示我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将自己放置在全人类的文学园地,采撷适合我且促进我的各种营养,在本民族的语境和现实中来书写我的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离不开文学谱系,也离不开前辈作家们。我再次重申,优秀的作家都是“作家中的作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作家中的作家”不是特别的褒扬之词,而是历史事实的存在。北师大张柠教授是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大家,给予《卡夫卡的妄想》以较高评价,这是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更是给予我自信、勇气和力量。我不在乎别人称呼我是“中国的卡夫卡”或“长安的卡夫卡”,我只是我,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立于长安这片古老的土地,以我的思考,以我的意识,以我的任性,沿着全世界文学前辈开辟的文学之途不断向前,建立我的文学“小秩序”,并在顺应人类文学“大秩序”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努力和探索。
邓琪:事实上,和经典文学保持对话关系,仿佛是您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征。您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寻找这种精神联结的?
冯北仲:如前所说,世界上所有优秀的作家都离不开世界文学的谱系,更离不开对本民族文学的坚守和拓展。向经典文本致敬,与经典文本对话,是优秀作家的必修课,而且及格分应在85分以上。我在高校从事《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史》教学,深谙文学经典对于一个作家成长的重要性。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隐性的,是看不见的精神力量,像一条绵长的时间河流,从古代而来,经过当下,奔向未来。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作家,凡是优秀的或者走向优秀的作家,都属于人类精神河流中的一员。我是一位理性的写作者,之所以选择写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是中国陕西人,很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作为中国的作家,只有深谙本民族的文学经典,以独立且独特的姿态面向世界文学,择优而吸收,才能创作出中国语境里的开放型的文学作品。
邓琪:您认为评价一本好书的标准是什么?除了小说中已经呈现出的经典外,对您影响较深的作家和作品还有哪些?
冯北仲:我个人认为,一本好书必须是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备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擅长和喜好,因素比较多,因人而异。当代,对我影响较深的作家是贾平凹。自小就喜欢读他的作品,尤其《满月儿》让小时候沉默的我变得喜欢讲故事的我。古代,除了最欣赏的《红楼梦》以外,我还喜欢《庄子》《金瓶梅》《儒林外史》《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等等。
邓琪:在作家的身份之外,您还是一名高校的学者。贾平凹先生称:“文学上,冯北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是否如鲁迅文学院徐可副院长所言,“别样的境界和格局”与您“学者型作家”的创作思维、创作方式有关?
冯北仲: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与我的创作思维和创作方式有关。在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在年轻时(二十岁左右)便开始写作,认为通过写作可以改变命运,争取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成功。而我不是,已有工作和生活经历的我,在读研究生时,也就是即将毕业时做了选择,决定投入创作。写作,是我在很成熟之后的理性选择,带着对学术的质疑,力求寻找一条“别样的学术路径”完成我的学术理想。我放弃了读博,毅然选择了写作。有评论家说过,中国当代文学看陕西,足以证明陕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高峰”地位,而且是以乡土文学著称。我的写作,立足于陕西乡土,又不完全是乡土,《遗园》里有不少农村景象和农人,但不局限于农村,重点写知识分子,从广袤的农村大地走出来的寻找精神立足和彰显人文境界的知识分子形象。我的写作,既继承了陕西乡土的传统,又带着人文思考;既是对传统写作的挑战,也符合我“求变”的精神气质。
邓琪:您的系列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书写对象——知识分子。严格来讲是高级知识分子。长篇小说《遗园》中的三代“守园人”自是不必多说,像《四块玉》里的影子、《带哨的笛声》里的展获、《卡夫卡的妄想》中的主人公“我”,都是如此。然而,对比您早期创作的《笔误》和《有狐》可以发现,把文学关注聚焦在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完善的事情。是什么原因,或者契机,让您选择从事高知题材的小说创作呢?
冯北仲:每个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那就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吧。熟悉的生活里,人人都是鲜活的、生动的、精彩的。我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几乎天天接触大学生、研究生、教授(海归的和本土的)。我的生活圈就是他们,是我最熟悉的生活。《笔误》的原型来自一个高校同事的人生经历,我进行了虚构和想象。《有狐》写的是一个女大学生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与高校有关。写作,是广阔的生活自动给作家过滤出可供选择的人和事,而不是作家随意选择想写什么。写出各种各样活色生香的人物,是每个作家的心愿,但只有写熟悉的,才能写出摇曳生姿的“格调”来,也才符合生活自身的内在逻辑。
邓琪: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其呈现的样貌各异。您认为当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生活焦虑,与其他时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冯北仲: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身的困境和焦虑,时代不同,呈现的方式也不同。古时的中国是封闭的,上自朝堂,下到黎民,一群人(包括知识分子)中不是善就是恶,不是正就是邪,两种势力在斗争。古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多是政治斗争带来的杀身之祸、株连受害、不得志引起的困境和焦虑。当下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古时的了,全面接受中西文化教育,享受世界文明带来的各种先进成果,是与世界同步的知识分子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焦虑,是传统观念与时代观念、传统风度与时代风气、传统职业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差异引起的,这是一个长久的“阵痛”问题,出现了复杂错综的各类“关系”,需要很长一段时期才能在“磨合”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焦虑,恰是一个时代最严重的病症所在。
邓琪:文学是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明的审美形象来实现其文学和现实意义的。而您的哲学专业研究更侧重于理性思辨和逻辑演化。两种不同的思维特性对您的小说创作影响如何呢?
冯北仲:我恰是在读哲学硕士期间决定了以后走“创作”之路,这是哲学给我的提示和指向。哲学是理性的思辨的,也是逻辑深化的。从这点上说,我确是个“独特”的人,没有把哲学的理性和逻辑当成一门专业来对待,没有当成客体的存在,而是直指我自身的思维体系,引我再三思考。我将所学的“哲学理性”转化为对“自我理性”的思考,我是谁?我去往哪儿?我与哲学“主客(天人)合一”了,这是我的性情和任性决定的,是一股说不清的力量指使的。也有人问我,学哲学的,也就是研究理论的,怎么能写小说呢?而且文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说法:作家不需要懂理论,懂了理论就受到束缚,写不出小说了。我认为全是片面之词。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决定了会从事和选择什么,内在(天分、性情、爱好)决定一切。文学是人类天生带有的基因,有的显示灵敏,有的显示迟钝。只要存有灵敏的基因,不管学什么,随着时光渐近,都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不需要任何刻意。哲学研究生三年,经过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一点不影响我后来的文学教学和写作,反而从逻辑上更让我明晰化,且加强了思辨性。哲学与文学,有关系也无关系,因人而异。对我来说,一边教授文学课,一方面文学创作,哲学让我的创作更趋于“独特性”,是我的惊喜,也是我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