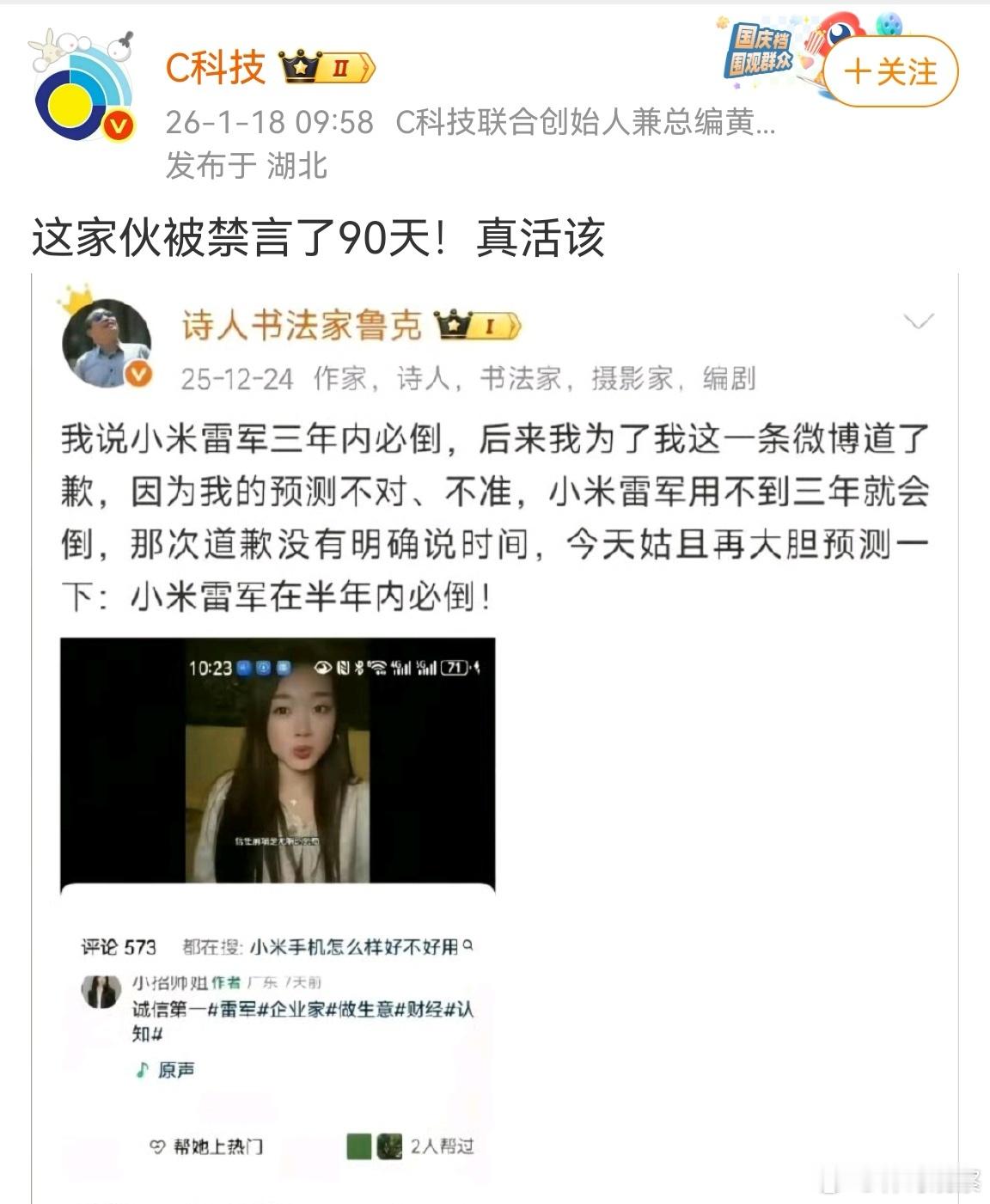小满前一日,地气翻涌。
茶馆后院那口老井,水面莫名涨了三寸,井水清得发暗,井壁的青苔绿得发腻,像浸了油的湿绸。手一摸,滑腻中带着点黏滞,竟像摸着活物的脊背,指尖还能感觉到细碎的颤栗。我蹲在井边看了半晌,水面映着的天是浑的,云走得飞快,可井水却纹丝不动——是地气往上顶,把井水硬生生托了起来,滞住了流转的气。
前门的风铃突然急响起来,叮铃哐啷,像被什么东西撞得发颤。

我转身回前堂,来人已经站在屋子中央。是个六十出头的老者,穿件深灰对襟褂子,浆洗得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脸色青得发灰,眼下一片乌青,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整个人透着股说不出的滞重。他怀里紧紧抱着个青花瓷瓶,十指扣在瓶身上,骨节绷得发白,像是抱着块烧红的铁。
“赵师傅。”他开口,声音又干又涩,像砂纸磨过枯木,“我姓孟,孟怀古,在城南开家小古董铺。我……我撞邪了。”
“坐下说。”我示意他对面的椅子,目光却钉在他怀里的瓶子上。
那是只康熙青花“婴戏图”瓶,胎质细腻,釉色莹润。瓶身上画着十几个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斗蟋蟀的弓着腰,放风筝的仰着头,踢毽子的踮着脚,画工精细得很,孩童面容饱满,衣裳的纹理都清晰可辨。可怪就怪在,所有孩童的眼睛都空着——不是没画瞳仁,是画了又被细细刮去,只留一圈白茫茫的釉色,像蒙着层薄雾,空空洞洞地对着人,透着股说不出的寒凉。
孟怀古坐下,把瓶子小心放在桌上,这才从怀里掏出块青布帕子,擦了擦额头的汗。那汗是冷的,帕子一沾,额头上竟浮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三个月前,我收了一张八仙桌。”他语速极快,像要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一口气倒出来,“紫檀木的,清中期的工,品相完好得很,就是……就是桌腿内侧,刻满了字。”“什么字?”
“符。”他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张折了四折的宣纸,双手捧着展开,是张拓片,“我拓下来了,您瞧瞧。”
纸上是朱砂拓印的痕迹,暗红发黑,像凝固的老血。确实是符,却不是道观里常见的敕令符,是另一种更古、更偏的符箓。符文扭曲如缠在一起的虫蛇,盘旋纠结,中间夹杂着些似字非字的符号,透着股阴鸷之气。我凑近细看,认出其中几个关键的字:镇、封、绝、灭。
“这是镇魂符,还是最狠的那种‘锁魂符’。”我指着拓片上一个螺旋状的符号,“你看这个,是‘锁魂扣’,意思是把魂魄锁住,永世不得脱身。再看这个像井字的图形,是‘绝地户’,封死所有往生的路。刻符的人,是铁了心要把什么东西永远封在这张桌子里,让它永世不得超生。”
孟怀古浑身一抖,椅子腿在地上蹭出刺耳的声响。
“桌子……桌子现在在我家后院柴房里,我不敢靠近柴房半步。”他声音发颤,牙齿都在打颤,“自打收了这张桌子,我就没睡过一个整觉。每夜子时,准时被惊醒——先是耳边传来细细的抽泣,像五六岁的孩子受了委屈,憋着不敢大声哭,气音丝丝缕缕,就贴在耳廓上,凉飕飕的。接着,就有冰凉的小手顺着裤腿往上爬,指尖划过皮肤时,像沾了井水的冰碴,激得人浑身发颤……”
他猛地撸起袖子。两条手臂上,果然有几道青紫色的细痕,指节分明,尺寸极小,正是五六岁孩童的手型,像印在肉里的阴刻,淡得近乎透明,却又清晰得触目惊心。

“我请过道士,做过法事,没用。”他把袖子放下,声音里带着哭腔,“符也贴了,鸡血也洒了,结果当晚哭得更厉害,那小手也摸得更勤了。后来没办法,我把桌子挪到柴房,锁得严严实实,以为能清净几天。结果……”他看向桌上的青花瓶,眼神里满是恐惧,“结果这瓶子,也开始闹了。”
“这瓶子和桌子是一批收的?”
“是。”孟怀古点头,手指虚点着瓶身上的孩童,“卖家说,都是从城西一间老宅里出来的。这瓶子收来时,孩童的眼睛就这般空着。可就在三天前,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这瓶子在冒气。”
“气?”
“白气,细细的一缕,从瓶口飘出来,在屋里绕了几圈,慢慢聚成个小人儿的形状,有手有脚,可就是没脸。”他闭上眼,喉结剧烈滚动,“那小人儿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最后趴在我胸口,不动了。我当时喘不过气,想叫叫不出,想动动不了,就像被钉在了床上,直到鸡叫头遍,那白气才慢慢散了。”
我起身,绕到桌前,仔细端详那个青花瓶。
青花的钴料发色纯正,是康熙中期的苏麻离青,晕散自然。画工更是精湛,孩童的神态、衣袂的飘动都栩栩如生。可那些空着的眼睛……我凑近了,借着天光细看,发现釉面被刮得极其干净,一点残留的钴料都没有,只留下一个个圆溜溜的小凹坑,深不见底,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窝,正对着人看。

“孟老板,”我坐回原位,“卖你桌子和瓶子的人,有没有说那老宅原来住的是什么人?”
孟怀古皱着眉想了想:“说是前清一个姓何的太医后人。那何太医专看儿科,在京城当年也算有点名气。宅子传了三代,民国时就败了,子孙散的散,死的死。这桌子和瓶子,是最后一个守宅的老仆拿出来卖的,还说……还说主人临终前吩咐,这两样东西必须一起走,不能分开,否则会出乱子。”
儿科太医。
镇魂锁魂符。
没有眼睛的孩童。
我脑子里的线,慢慢接上了。
“孟老板,伸手,我看看你掌心。”
他依言伸出双手。掌心细腻柔软,纹理清晰,是常年摩挲古玩养出来的手。可在他左手生命线的中段,忽然分出一条极细的支线,斜斜切入感情线,形成一个尖锐的三角。三角的顶点,正对着无名指下方——那是掌相里的“子息宫”,主子女缘。
“你,”我抬眼看他,语气放缓,“是不是有过一个孩子,没保住?”
孟怀古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椅子上,眼睛瞪得极大,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许久,他缓缓点头,声音轻得像叹息:“是……是个女儿,生下来没几天就没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内人后来也没再怀上。”
“孩子埋在哪?”
“西山……一个小土坡上,连块碑都没有。”他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时候穷,买不起棺材,就用块草席裹了,偷偷埋了……”
因果。
又是这两个字。四十年前失去女儿的伤口,四十年后找上门的、被封在桌瓶里的婴灵。这不是巧合,是债,是他心里那道四十年未愈的伤口,像一口枯井,引来了同样无处可去、无人祭奠的孤魂。
“那张桌子,”我重新拿起拓片,“不是普通的八仙桌。如果我没猜错,桌面的紫檀木,靠近中央的位置,是不是有一块颜色特别深,深得发黑,像浸了油,又像吸了血?”
孟怀古猛地瞪大眼睛,满脸惊愕:“您……您怎么知道?是有一块,巴掌大小,我以为是木头本身的结疤,还特意用砂纸磨过,可越磨颜色越深……”
“那不是结疤,是血。”我把拓片推回他面前,“年深日久,血渗进木纹里,和木头融在了一起。”
茶馆里静得可怕,连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穿堂风不知何时停了,空气凝滞得像一潭死水。后院的井忽然“咕嘟”响了一声,很轻,却在寂静里格外刺耳,像有东西在水里翻涌。
孟怀古的脸,从青转白,又从白转灰,没了半点血色。

“那张桌子,是‘药桌’。”我缓缓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前清的儿科被称作‘哑科’,孩童不会说病症,夭折率极高。有些孩子死得蹊跷,或是怨气重,家里人怕惹上邪祟,就请何太医处置。他便在这张紫檀桌上,给孩子做最后的净身,再用朱砂混着安神的药汁,在孩子眉心画一道安魂符,然后把孩子的生辰八字、死因,都刻在桌腿内侧——就是这些镇魂符。刻完用特制的药汁一擦,字迹就隐进木纹里,寻常看不见,只有用朱砂拓印,才能显形。”
我顿了顿,指着拓片上一个扭曲的符号:“你看这个,不是字,是‘夭’字的变体。这个是‘痨’,这个是‘惊’。每个符号,都对应一个死去的孩子,和一种死法。这张桌子,是一口活棺材,埋了上百个早夭的婴灵。”
孟怀古的手开始剧烈发抖,桌上的茶碗被震得叮当作响,茶水溅了出来。“那……那这瓶子……”
“这是‘魂瓶’。”我抚过冰凉的瓷面,指尖能感觉到釉下的纹路,“何太医做完法事,会取孩子的一缕胎发,或是一片指甲,用红布包好,塞进这种特制的青花瓶里。瓶身画婴戏图,是盼着这些早夭的孩子,能在画里寻个自在,不扰阳间。然后把瓶子供在药桌上,早晚各燃一炷香,连供四十九天,等孩子的魂魄散尽,再把瓶子埋在院子里。可这只瓶子,香没供满,法事没做完,何家就败了,那些孩子的魂魄,既没散,也没走,就被困在桌子和瓶子里,一困……就是上百年。”
“可这些孩子的眼睛……”
“眼睛是被刮掉的。”我叹息,“画瞳仁是给魂魄留了‘看’的口子,怕它们借着瞳仁看清阳间的景象,缠上活人。刮掉瞳仁,是想让它们眼不见,心不烦,安安分分待在瓶里。可越是这样,怨气越重——连看一眼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怎么会甘心?”
孟怀古闭上眼,两行浊泪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桌上,洇出小小的湿痕。他没擦,只是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所以……所以它们找上我,是因为我心里有我女儿的念想?”
“是因为你心里有个缺口。”我声音放轻了些,“你失去女儿的伤口,四十年了,一直没愈合,还在往外渗着悲伤和愧疚。这些婴灵,就像水往低处流,它们感觉到了同类的气息,感觉到了你心里的柔软和愧疚,就聚过来了。它们不是要害你,是想找个能接纳它们、给它们一个去处的人。”
许久,孟怀古睁开眼,眼里的恐惧渐渐褪去,多了种近乎绝望的平静。
“赵师傅,有解吗?”
“有。”我说,“但解的不是它们,是你自己。你得先把自己心里的缺口补上,才能给它们一个去处。”
“我?”
“你得先面对你女儿,再超度这些婴灵。”我起身,从书架顶层取下一个桐木盒子,打开,里面是画符的工具:朱砂、黄裱纸、狼毫笔,还有一小块暗红色的木头——是雷击枣木,辟邪渡魂最好的材料。
“这是雷击枣木,经天雷淬炼,能通阴阳,辟邪祟。”我把枣木放在桌上,“孟老板,我要你做三件事,一件都不能少。”
“您说,我一定照做。”
“第一,今天日落前,你去西山,找到你女儿当年埋的地方。带三样祭品:一碗温热的牛乳,一包软糯的饴糖,一件全新的红肚兜。不用烧纸,也不用磕头,就在那儿坐一炷香的时间,好好跟你女儿说说话。不用多,就说:‘爹来看你了,爹这四十年,从没忘了你,爹对不起你。’”
孟怀古重重点头,泪水又涌了出来,这次他没忍,任由眼泪往下流。
“第二,明天辰时,天刚亮,你带着这张桌子和这个瓶子,去城南十里的慈幼局。慈幼局后院有棵老槐树,树龄够久,阳气足,能镇住阴邪。你就在槐树底下,把桌子劈了——不用可惜紫檀木,就劈成烧火的柴。每劈一下,就念一句:‘尘归尘,土归土,魂魄散,往生路。’”
“那瓶子呢?也劈了?”
“瓶子不劈。”我从雷击枣木上削下薄薄一片,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了道往生符,符的中央,是一个极其繁复的“渡”字,笔画缠绕,却透着股平和之气,“你把这道符塞进瓶口,再用蜂蜡把瓶口封死,封得严实些,别留缝隙。封好后,在慈幼局后墙根挖个坑,把瓶子埋了,记住,瓶口要朝下。”

“朝下?”
“嗯。魂瓶养魂,口朝上,魂魄能自由出入;口朝下,是让它们入土为安,顺着地气归到该去的地方,不再飘零。”我把画好的符吹干,放在他面前,“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
我看着他,眼神郑重:“从慈幼局回来,你去城隍庙,捐一笔钱,请庙里的道长做一场‘婴灵超度法事’。不单为这桌一瓶里的孩子,也为天下所有无主、无祭、无名的早夭孩童。这笔钱,要从你古董铺的盈利里出,不能动家里的积蓄——这是你的赎罪,也是你的救赎。”
孟怀古没有半分犹豫:“我出!多少都出!只要能让这些孩子安心,能让我自己安心。”
“做完这三件事,你再回来找我。”我把雷击枣木符递给他,“到时候,我帮你把身上的阴债了了,把心里的缺口补上。”
他接过木符,紧紧握在掌心。那木符触手温润,竟隐隐透出点暖意,顺着掌心往四肢蔓延。
“赵师傅,”他起身,对着我深深一揖,腰弯得很低,“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你说。”
“等我把这些事都了了,我想在慈幼局旁边买块地,盖间小屋子。”他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我不卖古董了,就留在那儿帮帮忙,扫扫地,做做饭,照看照看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您说……这样行吗?”
我看着这个六十岁的老人,他背微驼,眼角布满皱纹,可此刻,眼里竟透出点亮来,像蒙尘的铜镜被擦净了一角。
“行。”我说,“那间屋子,要朝南开窗,窗台上摆两盆花。就摆茉莉吧,白色的,香得干净,能涤荡浊气。”
他笑了,是这半天来第一次笑,笑得很轻,却很踏实。他抱起桌上的青花瓶,这次抱得不再紧绷,而是多了点小心翼翼的温柔。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踩得很稳,再也没有来时的滞重和惶恐。
我送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夕阳西下,金红色的余晖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走了四十年,终于找到方向的路。

回到屋里,我拿起桌上那张朱砂拓片。那些扭曲的符箓,在渐暗的天光里,像一个个张开的、无声呐喊的嘴。我拿着拓片,走到后院,扔进那口老井里。
纸飘在水面上,朱砂遇水,慢慢晕开,红丝丝缕缕,像血,又像泪。片刻后,纸沉了下去,那些红色也渐渐散开,井水重归清澈,只是水面上,还留着一圈淡淡的涟漪,慢慢荡开,又慢慢平复。
我趴在井沿,看着水里自己的倒影。
倒影里,我的眼角,不知何时也多了一道极细的纹,像一道浅浅的刻痕。
是了。
这世间,谁心里没道口子?谁梦里没个哭不着、抱不到的人?那些口子,那些遗憾,白天我们用忙碌盖着,用笑容掩着,可到了夜里,它们就变成一口井,深不见底,映着所有我们不敢面对、又无法忘记的东西。
井水忽然又“咕嘟”响了一声。
这次,不像翻涌,倒像一声长长的叹息,轻得像风,慢慢散在暮色里。
(第七回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