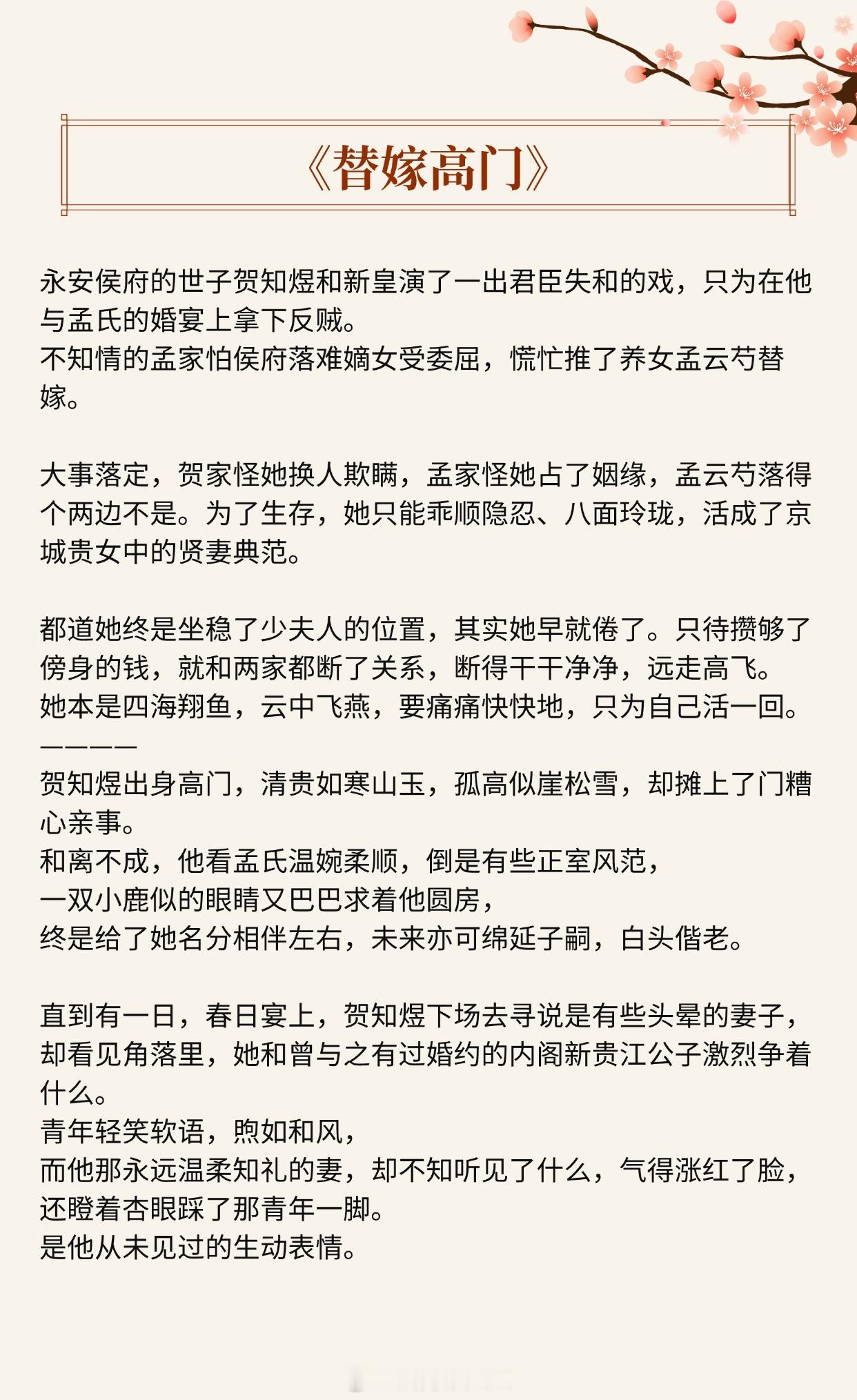再次见到季云羡时,我刚送走今天最后一位客。
他站在暮色里,风尘仆仆。
我站在暗巷中,颈间斑驳。
“虫娘,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比起那个被他抛弃,留在长安的冬天,
比起因他青梅走漏我身份、让我从名动长安的才女沦为营奴的那些年。
如今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我抬了抬倦怠的眼梢,朝他轻笑:
“奴家今日乏了,公子若想,不妨改天?”
木门合拢,他却突然伸手抵住,
“我顺利继承王位了,要是你想离开,我随时——”
“算了吧。”
我打断他。
十四年了,
北狄的王和长安的妓子,本就不该重逢的。
1
他抵门的力道大得吓人,我没再坚持,任由他进了屋内。
刚经历过云雨的房间并不好闻,他跟在我身后蹙眉屏息。
直到见我坐到浆洗衣物的木盆前,他才缓缓开口:
“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所有潜伏长安的北狄细作皆可赦归故土。”
“浸月有了身孕,我在此地不能久留。”
“……你要不要随我回去?”
我将生着冻疮的手浸入冷水,对着床单上浊白的污迹一遍遍搓洗。
“不必了,替我向王妃道喜!”
季云羡沉默片刻,最终叹了口气,蹲下身:
“当年是我与浸月对不住你。”
“你是北狄最优秀的细作,折损了你,我也很……”
“虫娘!”
一个瘸着腿的男人出现在门口,身上散发出的难闻气味让季云羡忍不住皱眉。
我却快速起身,擦干手上的水,拿了块手帕递到男人跟前。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男人下意识躲开我的帕子,用袖子随意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东坊的夜香收得迟了些……别!我自己来,好好的帕子别弄脏了!”
我摇了摇头,任由他将一只小陶罐塞进我手里:
“今天路过药铺时看见的,你留着擦手。”
他哈了口冷气,搓了搓冻僵的手指:
“快大寒了,你这门帘得加厚些,还有这院子也——”
话音一顿,宋星这才留意到屋内的季云羡:
“这位是……”
“一个过客。”
我转身,朝季云羡微微一笑::
“天色不早了,公子若想留下来过夜,得出钱!”
话音刚落,季云羡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腕:
“就算被罚没为妓,你怎么能跟夜香郎厮混在一起,你这样,你这样简直就是——”
“就是什么?自甘下贱吗?”
我接过话茬,目光落在宋星身上:
“夜香郎怎么了?我未必比他干净。”
从名动长安城的才女到人尽可夫的营妓。
夜香的气味洗洗还能散去,可我无论如何都洗不干净了。
“我和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罢了,公子若是嫌弃,就请早些离去吧!”
“虫娘,你从前不是这样的!!”
季云羡的声音追进屋里,我没有回头,只是拉着宋星的手关了门。
我早就忘记自己原先的样子了。
那个在草原上驯野马、挽强弓,在篝火旁饮烈酒、唱长歌的身影早在十四年前就被他留在了人不生地不熟的长安。
如今剩下的只是一个被故国抛弃的细作、被敌国羞辱的娼妓,以及——被爱人舍掉的弃棋。
2
屋里的烛火明了又灭。
屋外的人影终于离去。
宋星坐在桌旁,目光久久停在那块被季云羡留下的羊脂玉上:
“听说北狄有个习俗,夫妻两人争执,先低头者就送对方一块玉石,取化干戈为玉帛之意。”
“你想好了?真不跟他回去?”
盯着那块玉石,我的思绪飘到了更久远的年岁。
那时,季云羡不过是北狄王帐里最不起眼的八王子。
而我,已经是王庭暗中培养出的最好的探子。
一次,我在长安边境带回秘报的途中,偶然撞见了被手足们欺辱的季云羡。
彼时他因性情绵软,很不得北狄王喜欢。
他穿的单薄,蜷缩在雪地里,呜咽着朝我讨口热水喝。
我接下水囊递去并告诉他在弱肉强食的北狄,讨饭换不来生机,你得学会揣度人心。
后来,无人知晓的草场角落、废弃马厩旁,我教他如何从父王的沉默里辨出喜怒,
如何让兄弟的刁难反噬己身。
他学得很快,眼中怯懦逐渐被一种叫‘掌权’的欲望所取代。
我教他拉弓,教他射箭。
有一日,他忽然握住我执弓的手,指尖抚上手腕处那道被箭簇射伤的深疤,低声说:
“早晚有一天,我不会再让你过刀尖舔血的日子。”
为着这句话,我在北狄王重病,王庭内斗最严重的时候,毅然选择了他这个没什么继位胜算的八王子。
为了把他推上王位,我决定潜伏到长安,只为刺探出最有用的情报,给他在王庭中拉拢更多的势力。
一次,我为了暗杀三王子派往长安的使节受了重伤,筋脉尽断,好不容易逃到边城荒驿。
是季云羡冒着风雪赶来,将我救回王庭,衣不解带的守着我。
他说,就算我以后再也不能习武、拿刀、射箭,在他眼里我依旧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聂虫娘。
等到功成那日,他会……
话说到一半时,帐里走进一个身影。
那是北狄权臣的女儿,也是和季云羡上过一个书孰,有过青梅缘分的女子。
江浸月进来后,季云羡那半句话也没再说下去,
只是趁她不注意,往我手心里塞了块羊脂玉。
宋星不知道,在北狄,已婚男女送的玉石代表求和,
而未嫁男女之间的玉石则代表求亲。
就算季云羡不说我也知道,等他即位那天,会娶我为妻。
记忆被骤然拉远,我摇头苦笑:
“没拜过天地的算什么夫妻?我和他,是死敌。”
见宋星不再说话,我起身,朝他缓缓跪了下去:
“请大人转告陛下,虫娘绝不会让季云羡活着回到北狄!”
宋星的眼神顿时凌厉起来。
他站起身,抖了抖衣袖:
“那江浸月呢?她可是杀了你孩子的人!”
“季云羡说,她怀孕了。”
我俯身,眼中掠过一丝杀意:
“所以恳请陛下,允我一命还一命!”
宋星走后,长安城下了今年第一场雪。
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被季云羡抛弃的夜晚。
那是我来到长安的第十年。
烟月楼里,一曲唱罢,我同伪装成客人的同僚交换着最近的情报。
临走前,他有些于心不忍:
“你知道吗?八王子成亲了。”
3
策马奔回北狄的路上,我脑中还回响着同僚说过的话:
“这件事本不该让你知道。他娶了汝阳王的女儿,汝阳王说,只有这样他才愿意支持八王子继位。”
下马前,我无数次想象过和季云羡再见的场景。
我想过他会跟我解释,自己有多无可奈何,身不由己,
我也想过这会不会是他的缓兵之计。
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躺在曾经照顾我的暖帐中,和另一个女人翻云覆雨。
我发了疯地冲进去,扯开两人,用尽全力扇在季云羡的脸上。
就算是以下犯上,冒犯王威,我还是这么做了。
可他只是冷冷抬眼,问了句:
“谁准你回来的?”
我厉声质问他为什么背叛我和别人成亲。
他没说话,反倒是一旁盖着裘被的江浸月开口了:
“云羡哥哥,她就是你安插在北狄的那颗棋啊?”
“你也真是的!怎么把死物给养出脾气来了?”
她勾了勾唇,眼角划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嘲讽:
“棋子就是棋子,棋子是不能变成妻子的!”
我所有的理智在那一刻崩断。
下一秒,藏在袖中的暗器直刺她的咽喉。
随着一声脆响,暗器被季云羡挡下。
“放肆!”
他冷下脸色:
“聂虫娘,摆正你的位置!”
“若是你再敢对浸月不敬,我会让你后悔回到这里!”
浑身的血,比帐外的雪还要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长安的。
只知道再次醒来时,我躺在了一家陌生的医馆。
大夫有些责怪地看了我一眼:
“已经两个月的身孕了,怎么还深夜赶路?”
这时我才恍惚惊觉,
是两个月前,他瞒着我和江浸月定下婚约,独自一人来烟月楼找我。
那个晚上,让我怀上了季云羡的孩子。
做暗探这么多年,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走投无路。
我用鹰隼给他传信,希望季云羡能看在孩子的份上,让我回到故国。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自己身份暴露的消息。
大牢里,两个侍卫喝酒谈笑:
“听说这探子是北狄王妃来长安时说漏嘴才抓着的?”
“是啊,北狄新王带着王妃来谈停战,刚到长安,王妃在宴上多喝了几杯,当场就把她身份嚷出来了。”
“两国正在议和,陛下也不好重罚。”
“等议和事毕,说不定这女探子就能跟着北狄王回去了。”
“我看未必!”年长的侍卫冷笑一声,
“听说她和北狄王以前有旧情,王妃未必容得下她!否则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暴露她的身份了!”
指甲陷进掌心,血珠渗出,痛的我大口呼气。
“怎么,不甘心啊?”
我双眼猩红,看着身披雪白狐裘,缓步走近的江浸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是北狄人!”
“不!”
她面露嘲讽,打断我反驳道:
“你只是北狄的狗。”
“狗怀了主人的孩子,是要被当成妖孽,烧死的!”
我苦笑一声。
下一秒,藏在袖中的银针直刺她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