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年十月,也就是卢循天师道大军撤出建康近三个月后,刘裕打造的楼船舰队终于完工了。凭借这支强大的水师,足以彻底荡灭天师道。据《宋书·王诞传》记载,在这段期间后将军刘毅曾多次向刘裕请兵挂帅追讨卢循,试图摘一波桃子,洗刷上次的战败之辱,重振其政治威望。刘裕则“迟疑未决”,他毕竟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半辈子的行伍生涯让他军人习气很重,豪爽,讲义气,从前的同袍之谊总是放不下,此时正担任刘裕太尉府长史的王诞虽出身琅琊王氏,但早年曾担任过司马元显的谋主,颇懂高层政治权术,他看到刘裕犹豫,便秘密建言道:“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余人分之。(刘)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在王老师的教导下,刘裕终于洞悉了其中的利害,于是拒绝了刘毅的请求,让他留守建康,负责一切后方事务,并亲自领军,溯江而上追讨卢循。这一天是十月十四日。

在三月前七月十四日第一波负责追击卢循的辅国将军王仲德等人还被阻击在南陵(今安徽芜湖南陵县)一带,卢循大将范崇民领兵五千,在长江两岸屯泊了百余大舰,死死锁住了长江的江面。如今王仲德等人听说西征大军快要到了,他们坐不住了,决定打个胜仗为刘裕接风并开路。十一月,王仲德等人大破范崇民,焚其舟舰,收其散卒,并与刘裕军在长江上汇合。而此前庾悦与虞丘进也率军绕后占领了卢循后方的豫章。卢循的控制范围,已被压缩至寻阳这一小段长江之中。
如前章所述,从寻阳顺流至建康,轻舟一日可达,大队楼船也不会超过三天,然而从建康逆流到寻阳,轻舟得四五日,大队楼船总得十几天才能到。不管怎么算,刘裕至迟到十一月初也能杀到寻阳了,然而根据史书的记载,刘裕却直到十二月初一才与卢循在长江上开战,此前他的大军一直驻扎在距离寻阳东北百里的雷池(注1),“不越雷池一步”,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刘裕算过时间了,他七月中旬派出的那支从建康绕行大海掏卢循老窝的舰队,大概要十一月底才能杀到广州,在此之前,他不想过早与卢循展开决战,他担心卢循兵败后立刻逃归广州,如届时广州尚未克复,自己这局妙棋就白走了,卢循坚守岭南,则战事还不知道要拖多久。所以刘裕将水军驻扎在水位较低、无法进行大规模水战的雷池,主动避战而等待战机。
然而孙季高、沈田子的舰队居然比刘裕预计的要快了将近一个月。他们半路在临海郡(今浙江台州)得到了临海太守臧熹(刘裕小舅子)的大量补给,速度加快,到十一月初二就来到了广州外海。叛军果然没有料到刘裕这招,海岸上完全没有设防,孙季高舰队从珠江口进入珠江并来到距离番禺仅十几里的东冲(今广州南沙区东涌镇)时,城内叛军还毫不知情。但晋军只有三千人,而卢循留守番禺的军队尚有数千人,且城池坚固,一旦对方坚守时日,则战事拖延对晋军颇为不利。所以孙季高使用了当初卢循没有用的招数,烧毁所有船只,全军不留后路,迅速登陆,四面攻向番禺城。恰好当日大雾,守城士兵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只觉四面都是晋军,数量一定很多。于是守城军心崩溃,一日即城破。卢循的父亲卢嘏、长史孙建之、司马虞尫夫等人乘小船逃往始兴(今广东韶关)。孙季高与沈田子又做了个分工,孙季高留守番禺,沈田子则率军攻略始兴、南康、临贺、始安等岭外各郡。至此,岭南在被天师道军占据十年之后,终于回到晋朝的领土中。

十二月初一,卢循突然宣布,要率大军再度顺流而下去攻打建康!刘裕明白,卢循这是坐不住了,所以想跟晋军决一死战。刘裕算了一下时间,预计孙季高那边应该已经得手了,于是从容应战,率军雷池入雷江而进至大雷(即雷江入长江之港口)。十二月初二,卢循、徐道覆的数万水军也出动了,大船塞满长江,排成紧密阵型,前后都看不见舰队的头尾。天师道军虽然多次败在刘裕手里,但都是陆战,论水战,天师道军可从没输过,而刘裕虽然是常胜名将,偏偏从没打过水战,所以卢循、徐道覆对此战还颇有自信,觉得自己说不定能打败刘裕不败神话。然而刘裕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的水战水平到底能不能赢,他只担心一旦天师道军战败,他们会不顾一切冲下长江,从京口入海口冲向东海,回他们的舟山老根据地继续做海盗。所以刘裕还特意抽出两百艘战舰,命辅国将军王仲德率领前往下游的吉阳(今安徽东至县)设立封锁线,那里长江的航道比较窄,王仲德将战船并列停泊,横断江面,阻断天师道军可能的东逃之路。
由于天师道舰队多次打败晋军舰队都是借助船大优势撞击取胜,而这次刘裕建的楼船也颇高大,卢循楼船在体量上已不占优势,所以他想了个办法,将战船两两连接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双体舰船。这种船听起来很有意思,其实古已有之,如《战国策·楚策一》记:“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鲍彪注:“舫,併船也。”1975年山东平度东郊泽河东岸,曾出土一艘隋代沉船,船体下部由两船组成。两船间以方形木连接,木上铺板,形成整体。这证明中国古代确有此种船只,当是现代双体船的始祖。双体并联,耐波性及稳定性均较好,但灵活性有所下降,不如单船。如《晋书·顾荣传》记其为求快速,“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因而多用于军运(注2)。可这一次卢循却将战船连接在一起,船是大了,但如此就有了机动性的弱点。所以刘裕想出一妙招以为应对,那就是模仿周瑜的火攻!

首先,刘裕偷偷分了一支步骑兵登陆长江西岸。这些步骑兵带了大量纵火的工具,在西岸沿江小山中埋伏起来(在今江西彭泽县马当镇一带),等待时机,对天师道军队发动致命一击。
接着,刘裕命令所有轻快斗舰,列队在前,准备迎击。刘裕亲自提着战鼓,拿着令旗指挥战斗。右军参军庾乐生是颍川庾氏的孑遗,门阀出身的就是胆小,他慑于天师道舰队的惊人气势,登舰后竟然畏敌不进。刘裕二话不说,将他斩首示众。于是众军踊跃争先,逆流冲向敌舰。
晋军军舰上都装有在建康保卫战中立过大功的“万钧神弩”。其射出的箭威力极大,“所至莫不摧陷”。所以晋军轻舰的战术就是利用灵活的机动性逼近敌舰,然后保持一定距离对其进行压制射击,射得船上贼兵不敢冒头。然后,刘裕再利用这个时机,将自己的主力楼船舰队集结起来,利用风水之势,将天师道舰队压向长江西岸小山方向停泊。这时候就是埋伏在岸边小山上晋军发威的时候了,他们取出准备已久的火具,点燃火把,投向敌舰。这时东风大起,天师道舰队纷纷起火燃烧,烟炎张天,因其两船相连,点着一艘就等于烧了两艘,所以效率极快,不一会儿靠岸的船就全都着火了,整个江面一片火海。船上的可怜天师道军士要么被火烧死被烟熏死,要么跳入冬天冰冷的江水中淹死冻死。其他敌舰见状,纷纷转舵向寻阳溃逃。晋军水陆一齐追杀,至夜乃归。

逃回寻阳后,卢循、徐道覆知道大势已去,如今只能溯流而下沿赣江跑回岭南了。为了防止晋军追击,他们决定在赣江流入彭蠡泽的最狭窄的水口处,一个叫做左里(又名左蠡,在今江西都昌县西北左蠡山下)的地方据险阻截追兵。他们照抄刘裕在保卫建康时实施的战术,在江口打下木桩,在沿岸设置木栅。当初刘裕就是凭借着这样的秦淮河工事以两千人挡住了天师道军一波波的猛攻。既然刘裕可以,他们觉得自己可能也行。
十二月十八日,也就是大雷之战后第十六天,刘裕大军从长江进入彭蠡湖,又追至左里,被木栅所拦,不得前进。于是,左里之战爆发。
这次刘裕仍然亲自执令旗指挥,但就在这时,令旗的木柄突然折断,旗子飘落到湖水之中。大家感觉有点害怕,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想请刘裕暂且休整,来日再攻。刘裕却笑道:“往年覆舟之战(当年刘裕驱逐桓玄之决战),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

当年参与覆舟山之战的晋军建义功勋总共也不过一千六百多,如今还追随刘裕并打到左里的人估计最多不过两三百,而且多是中高级军官,无论当时真相如何,估计也不会有人拆穿。刘裕说这话,说得煞有介事,大家自然也就信了,于是一场军心危机消弭于无形。
晋军此战仍然是水陆并进,以优势兵力猛攻木栅,天师道军也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皆殊死抵抗,但仍然抵挡不住晋军的猛攻,上万人被杀死、淹死,其余也大多投降。卢循单舸逃亡。刘裕赦免了所有号称自己是被天师道军胁迫的投降军众。经此一役,天师道军已没剩多少实力,派遣将领追击就可以,刘裕还是不宜离开建康太久。于是,刘裕派兖州刺史刘藩、中军参军孟怀玉率轻装部队继续南下追击卢循、徐道覆,然后领大军凯旋建康。
大败之后的卢循、徐道覆一路南逃,沿途收拾残兵败将,居然还有数千人,觉得割据岭南似乎还够用,于是一路退到始兴,这才得知番禺城的老窝已被晋军从海路占领。于是徐道覆留守始兴,卢循则带上自己的兵,沿途召集旧部,南下反攻番禺。此时,晋军追兵刘藩、孟怀玉等部已南下追至始兴,沈田子也从番禺北上杀来,三支部队遂一起围攻徐道覆。义熙七年(411年)二月初五,也就是天师道军在左里战败之后仅一个半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先将妻子儿女毒死,然后自杀。
与此同时,卢循一路召集旧部也杀到了番禺城下。他毕竟在此地经营七年,信徒很多,没多久又聚了一万多人来攻城。城中当时仅有孙季高一千余晋军守城,固守二十余日,形势危急。已占据始兴的沈田子就与刘藩商量说“广州城虽险固,本是贼之巢穴。今(卢)循还围之,或有内变。且季高众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贼还据此,凶势复振。下官与季高同履艰难,泛沧海,于万死之中,克平广州,岂可坐视危逼,不相拯救?”刘藩认为有理,便兵力交给沈田子,让他率军南下救援。
四月,沈田子大军又杀回了番禺,与孙季高内外夹击,一举击溃卢循,杀敌一万余人。卢循众散(注3),最后只带了三千残兵再次逃亡交州,沈田子、孙季高一路追杀他至苍梧、郁林、宁浦,卢循虽一路损兵折将,但仍在宁浦港口坐船逃入了大海,恰好这时孙季高生了重病,晋军遂打道回府,将剿灭卢循残党的任务交给了交州刺史杜慧度。而孙季高还没能回到番禺,在半路的粤西的晋康郡(治元溪县,今广东德庆县东)就病逝了。刘裕对他相当惋惜,后来追赠他为交州刺史。
四月二十四日,卢循从海道逃到了交趾,纠合当地的俚、獠族人,合计八千多人(卢循三千,俚、獠族人五千多),试图攻占交州治所龙编(今越南河内东)。杜慧度率本府六千人应战,战前,老杜把自己家的财产全部散发给军士们做奖赏,以提振军心。结果一战下来,卢循舰队被毁,部众溃散。他自感末日来临,决意跟随他十年前的老教主孙恩投水去当“水仙”。他先毒死了妻子和子女,又召集众姬妾,问:“谁能从我死者?”

才不过短短十年,信徒们的狂热已经消逝了,除了少数几个死忠者外,女人们大多不想当“水仙”,只说:“雀鼠贪生,就死实难。”
听到这话,卢循脸上露出了悲凉而凶狠的神色,他放过了那些愿意陪自己死的姬妾,而将那些贪生怕死的姬妾全部杀掉,然后狂笑着投水而死。至于那些说表示愿意跟着殉葬的姬妾最后到底有没有随他而死,那就不得而知了。
杜慧度军将这些人的尸体打捞出来埋葬,又将卢循一家的尸体斩首,人头送往建康报捷。席卷了东晋几乎所有州郡的天师道之乱,在荼毒南方整整十二年后,终于被彻底平定。此后,道教的信徒们对主流文化做了全面的屈服,放弃了在政治方面的抱负,并开始借鉴葛洪的道法思路,对道教诸多反社会、反政府的BUG进行修复,并增订了斋戒仪范和戒律(注4),从而使道教的内容更加净化,也更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
最终,在北天师教教主寇谦之与南方上清派(茅山派)祖师陆修静、陶弘景(注5)的努力下,道教披上官方化的外衣,转向了儒学化、上层化(注6)以及与世俗脱离(注7)的发展道路,得以流传至今。

注1:当时长江北面的一个湖泊,以一条雷江与长江相连,其位置在今安徽宿松的大官湖、龙感湖、黄湖、泊湖一带,它南濒长江,北倚香茗(属大别山脉系),河湖交错,水路参差,向为兵家必据固守之地。
注2:田昭林:《中国战争史(全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22页。
注3:唐刘恂《岭表录异》:“卢亭者。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今大屿山,香港岛和万山等岛屿),野居,惟食蚝蛎,垒壳为墙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泉郎,即此州(指福建泉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叛逃,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
注4:《魏书·释老志》载寇谦之假托神道,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即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即入教所缴纳的五斗米)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加以服食闭练”。所谓“合气”,就是合男女阴阳之气。按马伯乐的说法,就是“用一整套复杂的性交技术来进行性滥交”,据说可用这种方法求得长生。东晋玄学士族举办的性聚会亦常以此为名,乃至“男女杂沓,如野兽然”。参阅【法】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517-541页。以宗教为名行禽兽狂欢之事,这自然是不为中国传统名教所容的。这种对生活的反叛以及群体的骚动,和真正的社会反叛亦有一种潜在的联系,所以道教想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必须禁止这些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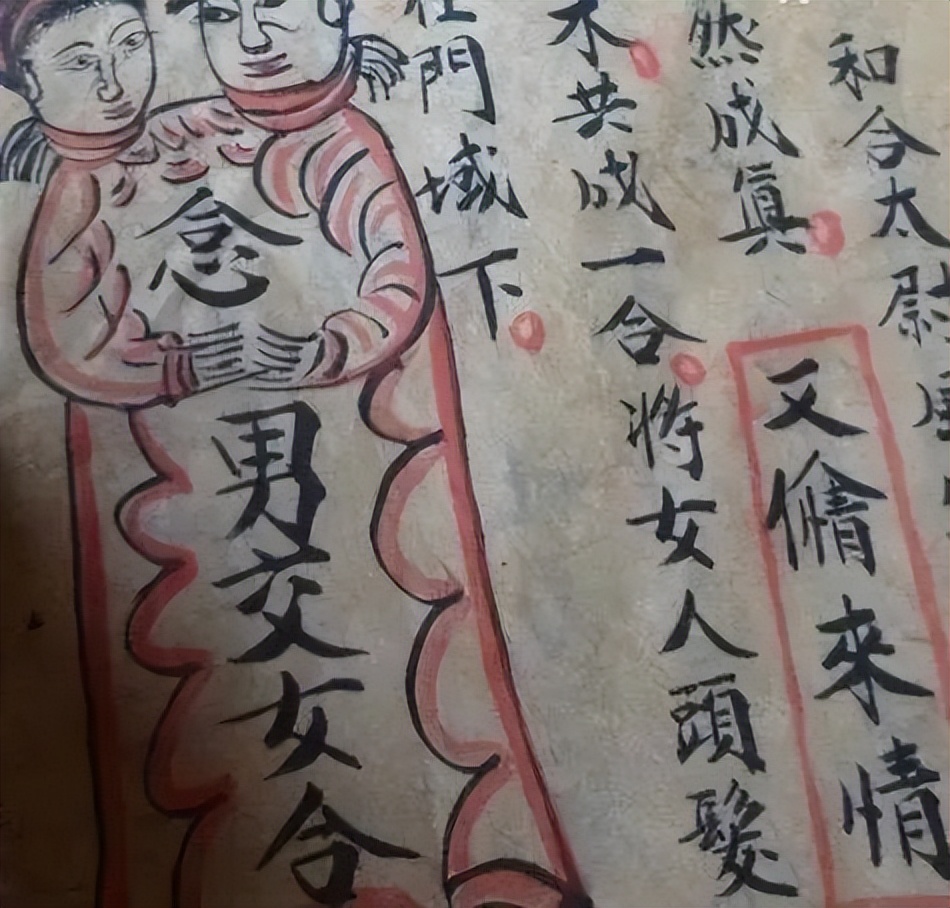
注5: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一文就通过对茅山道教三茅君信仰的分析论述,指出陶弘景《真诰》中便利用了当地的白鹤庙信仰传说,将之与仙传糅合,转化为三茅君乘鹤的情节。通过这种述说方式,“神仙侨民”三茅君(三茅君原籍咸阳南关)实现了土著化,成为江南新乡土的护佑之神。显然,土著化了的江南侨民们,更愿意接受一个经历相似的神祇,融合侨、旧两种色的神仙三茅君由此获得了成长空间。三茅君对于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也使其很容易为旧民所接受。这是在侨旧融合的政治体制下,侨旧民众相互作用而带来的一种协调。参阅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收录于《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95-137页。

注6:寇谦之的传道,使北魏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符箓,自称“太平真君”,改元为“太平真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道君”皇帝,且“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就像欧洲的皇帝进行宗教仪式的加冕礼一样。而南朝陶弘景的传道,则使茅山成为当时道馆最为集中的修道圣地,山中道馆多是皇帝敕建或得到士族官僚供养,与世俗权力世界形成相当密切的信仰关系和运作模式。陶弘景影响建康政治,甚至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参阅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412-413页。
注7:从齐梁之际开始,天师道教团开始脱离世俗,入山建立道馆,它们自称“上道”“上经”“上法”,对旧天师道修法多有批判,贬之为“下道”、“小道”或“下科”。其受众主要是那些有意愿脱离世俗、追求神圣的修道者,其中当然也包括天师道信徒。参阅孙齐:《山中的教团:中古道教“寺院主义”的起源》,收录于《新史学》第十四卷: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与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