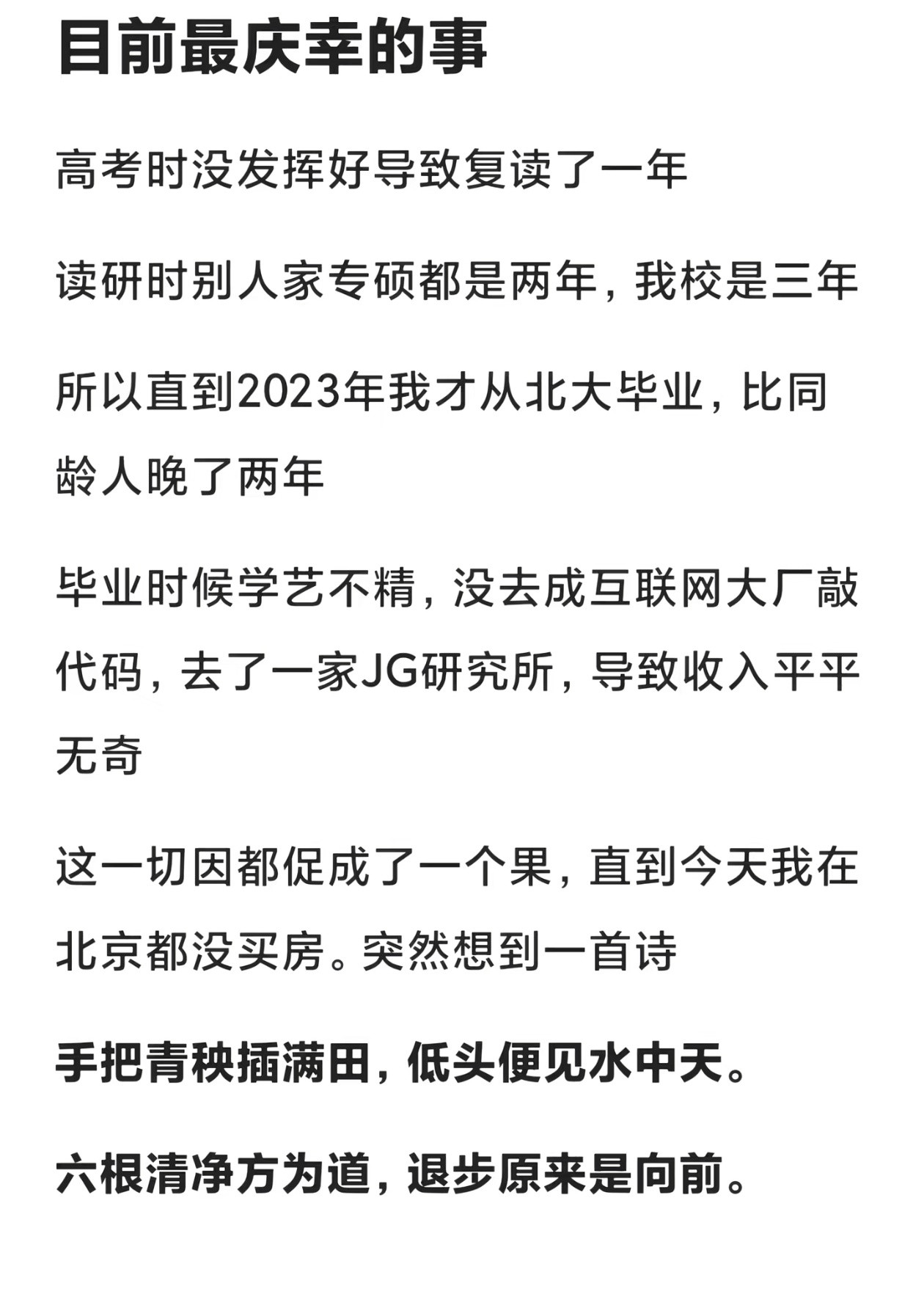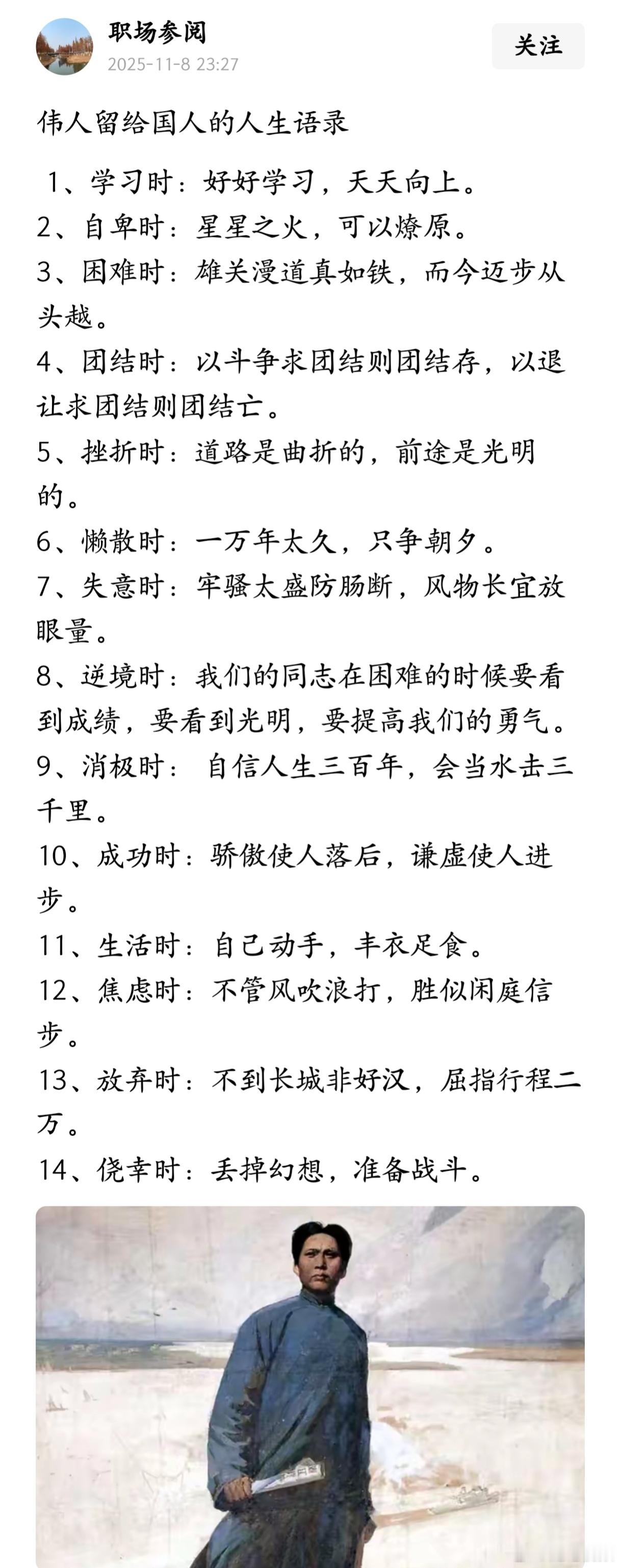作者:黎荔

我是一块卵石,早已忘记自己最初的模样。河水日复一日地抚摸我,那种抚摸既温柔又残忍——温柔在于它的持之以恒,残忍在于它的不可抗拒。现在,我是如此圆润,像一句被反复打磨的箴言,表面长着一层毛茸茸的青苔,那是时间为我披上的外衣——柔软、湿润,是生命在我身上短暂停驻的印记。淤泥和细砂在我身侧沉淀,如同往事层层堆积。
我曾是一块有脾气的岩片,带着山崩时的怒意坠入河谷,可如今,连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但奇妙的是,即便千万颗卵石躺在同一段河道,也无人能复制我的曲线——那是时间与水流共同签署的唯一契约,是命运以水为笔、以我为纸写下的不可重印的签名。我的曲线偏向左侧,形成一个微妙的凹陷,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永远填不满的东西。天然的赭石底色上,散布着乳白色的纹路,像远古的星图,又像干涸的河床记忆。
隔着流动的河水看我,你永远看不清真实的我。阳光穿透水面时,我周身泛起金色的光晕,像一块温润的琥珀;月光洒下时,我则化作幽暗的影子,仿佛深水中沉睡的秘密,随时会融化进夜色里。这两种样子都是真的,也都不是真的——真实是多重曝光后的模糊影像。
我依靠感觉生存。这不是人类那种需要神经与大脑的复杂感觉,而是更为本质的、与流水同频的震颤。我能感觉到雨季与旱季的交替——雨季时,河水变得急躁,裹挟着上游的泥土和枯枝,冲刷着我身上的每一道纹路;旱季时,河水消瘦,我的肩膀会偶尔露出水面,感受风的触摸。我知道春天融雪时水的刺骨寒冷,也知道盛夏午后阳光穿过水面的温暖光斑。我能分辨出渔夫的竹篙与游船的桨声,也能听出独木舟的轻盈和货船的沉重。
最清晰的感觉,是那些被称为“命运”的东西从头顶驶过。最早的,是独木舟,轻得像一片落叶;后来有了木船,船底会轻轻蹭过我的头顶,留下木质的叹息;再后来,钢铁的巨物轰鸣而过,它们的影子庞大而冰冷。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声音和重量,而我,只是静静地记录着这些声音在水中的折射。
我的记忆比任何生灵都要长久,也因此更加模糊。我记不清是第一千个春天还是第一千零一个春天,有一只翠鸟曾站在我的肩上整理羽毛;记不清是哪个黄昏,一个少年赤脚踩过我,去追逐漂流的木枝;也记不清是哪只青蛙,曾在月夜跃过我的头顶,它的肚皮在月光下泛着银白的光,像一道小小的闪电。我看鱼群如何躲避鹭鸟的袭击,看水蜘蛛如何在湍流中结网,看落叶如何在水面旋转,像跳着最后的舞蹈,看一艘载着逃难者的木船从我头顶掠过,桨声里裹着哭腔……这些细节像水纹一样扩散、消失,只留下一种感觉的余温。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只蜻蜓的死亡。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它停在我身上的青苔上休息,翅膀薄如幻梦,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它只停留了片刻,对我耳语了几句关于高处的风景,忽然一阵急流,它被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的长久,是用无数短暂堆砌而成的纪念碑。
还有一个人,站在河岸高处,手指远方,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我不知道他指给谁看,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但那一刻,他眼中的光芒,我至今记得。他的手臂伸展的弧度,他声音中那种混合着希望与恐惧的颤抖,都随着水流渗进了我的肌理。那个人早已化为尘土,他的后代的后代也许都已不在,但那指向远方的姿态,却永远定格在我对那个午后的记忆里。
他们都消失了,像水面的涟漪,出现又消散。而我还在,依旧躺在这里,看河水把他们的故事卷走,又把新的故事送来。在漫漫岁月中,我继续存在。存在也可能是漫长的等待,是不断失去边际的过程。每一天,河水都从我身上带走些什么——也许是亿万分之一的我,也许是一段记忆的片段。那些微粒碎片随波逐流,有的沉积在下游的河床上,有的被冲进大海,有的附着在鱼鳞上去了未知的地方。我的一部分正在逐渐散落,成为这条河另外的脚步声——在远方,在看不见的地方,继续行走。
有时候我想,也许我已经不是最初的那块石头了。岁月不仅磨圆了我的棱角,还一点一点替换了我的物质构成。现在的我,是原始内核与无数沉积物的混合物,是自身与他者的结合体。那么,“我”究竟是谁?是那个最初从山体崩落的碎石,还是这条河用时光塑造的艺术品?那些清晰的边界——我从哪块山岩分裂而来,以及我最初的形状——都已经融入了河水的吟唱。我不再是完整的我,而是流动的我,是不断变化又始终保持某种本质的我,参与着一场永不停息的自然流动。
我滞留在一条河不为人知的深处,见证了创造与取消的无尽循环。春天的藻类在我身上生长,冬天的寒流又将它们带走;夏天的鱼群在我周围嬉戏,秋天的萧瑟让它们藏匿无踪。自然热衷于创造生命,又痴迷于取消它们,如同一个孩子堆起沙堡又亲手推倒。河水不断创造新的波纹、新的光影、新的生命,又在下一刻取消它们。就像那只蜻蜓,它的到来是一种创造,它的离去是一种取消。而创造与取消之间的那个瞬间——停驻在我背上的那片刻——便是存在本身。领悟到这一点,在这场宏伟而无意义的游戏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是一块会记忆的石头。我的每一道划痕都是一个故事,每一片青苔都是一段时光,每一处凹陷都是一次等待。我记录着河流的心跳,见证着生命的来去,承载着时光的重量。
如今,我的边缘还在继续消逝,继续漂流。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完全消散,化为无数微粒,散布在这条河的每一处。但每颗微粒都会记得,自己曾是一块完整的卵石,曾在某处河床上,静静地感受过千年的流水,见证过无数生命的绽放与凋零。我并不悲伤。悲伤是短暂生命的特权。我活得太过长久,已经学会了不悲不喜的智慧。我只是见证,只是感受,只是存在。在河水的永恒流动中,我找到了静止的方式;在万物的不断变化中,我找到了不变的自我。
有人说石头没有心。可若无心,怎会懂得等待?怎会记得温度?怎会在千年万年之后,仍为一片落叶的飘落而微微震颤?我不是无情之物,我只是选择沉默。因为言语会被风带走,会被浪打散,而沉默却能在水底沉淀成永恒。如今的人类匆匆走过河岸,举着发光的方盒子,拍下“自然之美”,却从不曾蹲下来,听听一块卵石的心跳。他们追求独特,却又批量生产着相似的灵魂。而我,这颗被遗忘在河心的卵石,无需宣称个性,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唯一”的最好诠释。
河水依旧流淌。明天,或许会有新的船驶过,新的蜻蜓停驻,新的人指向远方。而我将继续躺在这不为人知的深处,以青苔为袍,以淤泥为枕,任时光在我身上刻下无人解读的纹路。